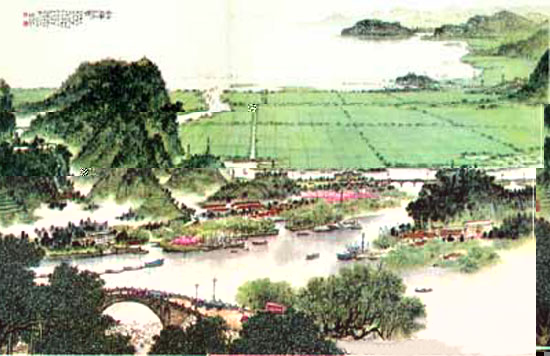今年春节已是早春时节。乘火车在平坦无垠的华北平原驰骋,窗外掠过的满眼皆是绿油油的麦田。在这个季节的华北大地上,麦绿绝对是最赏心悦目的颜色了。举目望去,四海无闲田。
家乡亦是此景。更有勤劳的农人,已经趁着春节的空闲,早早浇起了返青水。节后走亲访友期间,大家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浇完麦子返城务工的计划。看得出,大家并不焦虑,虽然去冬少雨,但河塘沟渠里水源充足,小麦灌溉不成问题。
真正的忙碌要待大规模春浇开始以后,到那时,许多回乡过年的年轻人已经返城务工,父母照例会帮他们把返青水浇上,然后中年男子再进城,妇女们则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小孩,负责田间管理,其中许多人还会找一些小手工艺品加工的活来做,村庄又恢复日常的状态。此后,夏秋两季农忙时,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又会短暂回乡,紧张地完成收播后再返城。一年三次周期性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家乡最基本的生活节律。
这种半工半耕的模式已然构成农民生计的常态。在中国式的家庭伦理支撑下,它往往采取家庭分工的形式。在家乡农村,家庭分工由大家庭的代际分工和小家庭的性别分工组成。中年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在家,年轻人在孩子年幼时也是如此,孩子上学后则男女一同外出,中年妇女的留守责任中便多了一份子女家庭的事务,无论双方是否分家。不过,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年轻子女会在农忙时回乡。
正是依靠这种生计模式,家乡人民把农业经营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如今,村里没有半点荒田,所有的农地都被充分利用起来。冬小麦和夏玉米的亩产都在千斤以上(当然玉米产量要高一些),扣除生产成本(不计人工)后,亩均纯利至少相当于一季农作物的收成。农业收入虽然在农民总收入中占比已然不及一半,但必不可少。特别是随着年龄见长,务工收入逐年下降,农业收入却相对稳定,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会重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有主动放弃农业的家庭,从二三十岁刚成家的年轻人,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在经营着自己的土地。农业生产显然比城市务工对劳动力更具包容性。
除了生计所需,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和生产条件改善也是农民不愿放弃农业的非常关键的原因。
如今,除了灌溉和必要的植保措施需要人工外,耕、播、收等环节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小麦和玉米皆是如此。全村仅大型联合收割机就有七八台,作物收割后秸秆直接粉碎还田,小麦可以直接在地头卖掉,玉米运回家脱粒后也很快可以卖掉。以前两季农忙都要持续半个月之久,起早贪黑辛苦非常,如今不光时间缩短一半以上,劳动强度也大为降低。机械化程度提高使得种田变得简单轻松,技术门槛变低,即使从小没怎么干农活的年轻人也不难掌握,这是全村几乎所有成家后的年轻人都保留承包地耕种的重要原因。
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则是近年来家乡农村发生的最让人惊喜的变化之一。我们村大量农田地势低洼,属盐碱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大规模水利建设虽然改造了不少,但由于后来农民两工取消,水利建设基本停滞,水利设施几乎全部瘫痪,灌溉靠打井,排涝则只能靠太阳晒,导致存在大量荒田。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争取到一些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开掘疏通了环村的主干渠道,使全村水系与德惠新河贯通,保证了水源充足,彻底改变了以往灌溉靠打井的局面。加上深入田间的次级渠系也得到一定修复,排涝问题也基本解决,水利条件的改善反倒让农业开发项目建设的机井泵房变成了摆设。另外,新修的机耕道和经过平整后的土地,虽然存在一些工程质量问题,但毕竟改善了机械作业条件,为机械化程度提高打下了良好基础。上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为政府投资,农民没有出一分钱,却切切实实享受到了生产条件改善带来的耕作便利。目前存在的隐忧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完工后如何更加有效的管护,以保证其使用年限尽可能延长。现在有的农户蚕食老的机耕道,往沟渠里倾倒生产生活垃圾甚至毁坏沟渠的现象屡见不鲜。几条前几年挖的渠道由于缺乏清理,如今已出现淤塞,长起了荒草杂树,估计不出几年就有报废的可能。从我在其他农村调查的经验来看,农业基础设施(其实也包括公共生活设施)的管护依靠农民个体积极性或农民合作是不现实的,关键还是要靠基层组织发挥作用。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外一个必不可少却有违政策法律的因素是,这些年村里一直都在调整土地。除了2012年因铁路建设征用土地而进行的大调整外,其余都是各村民组内部的小调整,不外乎减人减地增人增地,这种情况每年涉及的户数很少,仅靠小组内部即可平衡。绝大多数农民把土地调整视为理所当然,它带来的是土地在农户之间的相对公平的分配,这对八零后一代年轻人来说尤其重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家乡人传宗接代观念很重,出现了不少多女户,五个女儿的就有好几户。如今这些家庭的女儿皆已出嫁,若不进行土地调整,这些家庭占有的土地数量必然很多。对于结婚生子的年轻男子来说,小家庭新增加的人口若分不到土地,将出现全家仅一口人土地的情况。正是由于土地调整,使得村里的年轻家庭都获得了相应的土地。当然,让哪家拿出土地都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土地调整一直存在阻力,并非每个小组年年都能内部结清平衡账,有的隔两年,有的隔三年,需要土地的多了,舆论压力自然就大了,不愿拿出土地的家庭占了几年“便宜”也就见好就收,所以土地调整总能实现。不过,土地调整显然是违反“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的,农民也并非不知道这个政策,但由于多年来已形成地方习惯,所以目前尚未出现大量上访的情况。
通过土地调整,不仅仅实现了土地的相对公平分配,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减少了土地细碎化。众所周知,土地细碎化是阻碍农业机械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区其影响更为关键。由于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和生产条件改善,地块远近和土质好坏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已经大为减小,像以前那样为求公平而搭配地块已无太大必要,这就为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提供了客观条件。由于农户分散且利益分化,依靠农民自愿协商调换土地解决细碎化问题的方式难度太大,实践中也没有大规模成功的经验。最现实的方式还是依靠村级组织进行土地调整,2012年那次大调整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土地细碎化程度,比如一组人均3亩地,以前至少分布在5个以上不同的地方,如今基本控制在三块以内,地块数量减少单块面积增加,提高了机械作业的便利程度。应该说,家乡最近几年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土地调整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土地调整的前景实在难言乐观。去年起市里按照省里安排开始搞土地确权,据新闻报道确权率已达百分之八十以上,今年将全部完成。有趣的是,我问了很多人,竟然无一人知道此事,更不知道确权是要干嘛。待我简单解释后,许多人的反应是“国家要把土地收回去了?”细问之后,才发现农民的逻辑是:地块边界本来就很清楚,并无多少权属问题,国家花这么多钱搞确权肯定有其他目的,最可能是要把土地收回去给大老板种,要是依然由农户经营,何必多此一举,多不划算?!且不讨论确权后的土地流转问题(尽管在主流话语中,确权目的是为推动产权交易),单是确权颁证后对土地调整可能造成的困难就很让人有些担忧。土地调整本是村民自治范畴内一项非常具有群众基础的事务,其灵活性恰可因应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流动带来的复杂变动的地权诉求。家乡的土地调整本就与政策不合,确权颁证势必造成村级组织协调难度增加,土地权属变动变更登记手续复杂,要么造成土地证变成一纸空文,要么农民借此拒绝调整土地,等等。土地调整是农民实现更加合理的地权配置的现实需要,土地确权则是主流话语中进行产权交易增加财产性收入的理论想象,二者之间的错位着实值得玩味。
生计需要的最优配置和生产便利性的提高,使得家乡农民惜地爱地并高效地经营着土地。除非行政强推,绝对多数农民不会主动把土地流转给他人,这与华北地区悠久强大的自耕农传统或许也不无关系。二姑和舅舅家所在的隔壁乡镇,重点打造了一个大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典型,对外号称规模几千亩,姑父和表哥们跟我说那都是糊弄上面领导的(去年某中央领导曾亲临视察),实际上只有承包原来镇里农场的土地面积数是真的,他们所在村的土地实际上并没有租出去。这个农场主在外做生意发了点财,给出的土地租金是每年1000元(补贴依然归农民),但正如姑父所说,一来租金太低,二来现在种地轻松,三来年纪大了不能出去打工,不种地干吗?60多岁的姑父代表了绝大多数普通农民的看法。1000元的租金几乎是农民私下流转租金(最高每年500多元)的两倍,农民仍然嫌低,这就说明他们的考量中经济因素并非是全部。租金更高的话,经营者,特别是种粮的经营者显然是承受不起的。同前些年一样,家乡农民仍然对土地流转很没有积极性,我看不出这种积极性有短期内提高的现实可能性。
许多人都有这么一种认识,或者担忧:农业比较收益低,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都是老弱妇孺,因此田地缺人耕种,粮食生产面临危机。我觉得我的家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证。这当然不是孤例,反倒是我们多年农村调查中屡见不鲜的常态。半工半耕是农业型地区农民最普遍的生计模式,这是农民因应城市化基于个体生存理性做出的最优选择,是农民种田的内在积极性。只要农业生产便利程度提高,这种内在积极性就可以顺利转化为更高的农业生产力。换句话说,目前农业生产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并非没人种田,而是有田不好种。因此,解决之道就不是不切实际地进行土地集中搞规模经营,而是因应农民需求,通过资源输入和制度调整提高农业生产便利化水平。我期待着包括家乡在内的农村地区,在改善农业生产便利程度上能够采取更多有突破性和实效性的措施,这是农业的希望所在,也是农民生计所系。
本文修改版发表于《中国老区建设》2015年第5期,此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