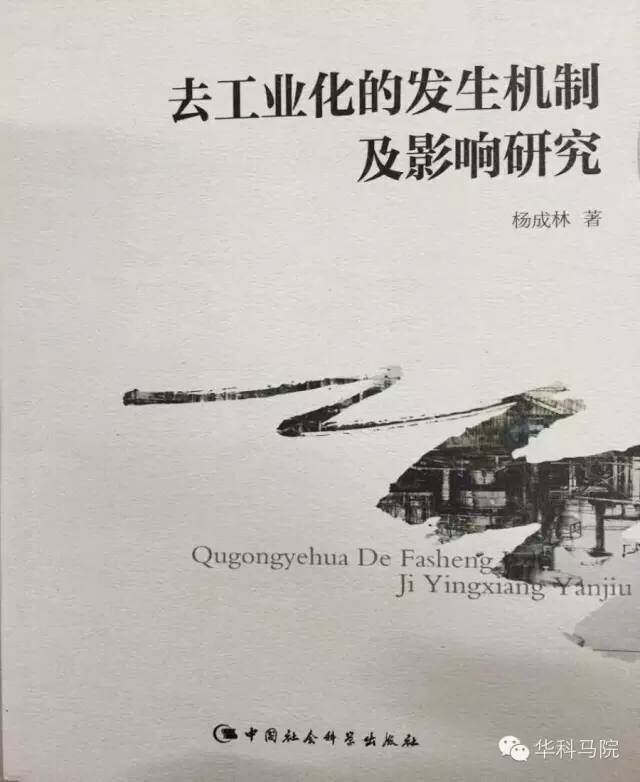杨成林:《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及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0月),书中阐述了西方世界的去工业化发生的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工业政策制定者深思。
作者简介
杨成林,经济学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现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及应用、经济去工业化、“三农”问题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改革》、《中国土地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等多项课题研究。
序 言
自20世纪50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先后经历了工业,特别是经济制造业的产出和就业份额不断下降的现象。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回应,一些社会学家和未来学者认为,这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演变过程,是经济不断走向高级化的过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社会学家丹尼斯·贝尔,他在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于1973年出版了著名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自此,去工业化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并由此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然而,在这些学者看来,去工业化是一种积极的经济现象,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不断有质疑其产业空洞化的声音出现,并提出相应的“再工业化”政策。但从总体上看,主流的声音认为,以服务业,而不是以商品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是经济社会向高级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但是,情况确实如此吗?或是服务业何以能够成为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基础呢?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尽管经济社会的发展有转向服务化的倾向,但工业制造业仍然是经济运行和增长以及创造财富的基础,而服务业的发展是为工业制造业服务的,或者说,制造业是服务业的基础和需求来源。
在卡尔多看来,工业经济中的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制造业不仅是增长的核心动力,而且是财富和价值创造的基础和来源。事实上,资本主义在过去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2008年的经济金融危机以及新近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都在经验上证明了工业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从而否定了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作为领域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基础和核心地位。这也是欧美发达国家再次提出经济“再工业化”的要义之所在。显然,在关于经济去工业化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上,去工业化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去工业化使经济丧失了运行和增长以及财富和价值创造的基础和核心动力。另外,如果去工业化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会发生工业制造业过早衰落,从而出现了消极的早熟去工业化呢?总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仍然是经济的基础和核心动力所在。
尽管如此,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界仍然认为,经济的去工业化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这不仅是意识形态使然,即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制度,而去工业化是这一制度向更高级演变的必然趋势,而且也主要体现在对去工业化的传统解释上,即去工业化是经济的内因,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因素的结果,即使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外部因素也对去工业化产生了影响,但这些影响相对于内部因素是较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解释根本没有触及到经济去工业化的深层原因,与此同时,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早熟去工业化的解释也同样如此。这是因为,如果去工业化是一种积极的经济现象,那么去工业化不会给出现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以及出现早熟去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造成经济上的种种困难。换句话说,仍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经济的去工业化现象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系统性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求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和根源。这既是理论探索本身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又是理论研究本身的魅力所在。
经济的去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但这一“特征事实”绝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积极的“特征事实”,对发达国家如此,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从现有的发生去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看,经济的去工业化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任何国家和任何地区都必然要经历经济的去工业化进程,其或是如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后出现的去工业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早熟去工业化。对已经发生去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如何获得“再工业化”政策的成功,或重塑工业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是当务之急;而对于尚未发生去工业化,或是已经存在去工业化迹象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如何避免经济去工业化的发生则是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对经济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和根源的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而这也是我们对经济去工业化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基本目的之一。
工业制造业的成长奠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同时造就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过去,依靠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尤其是过剩人口所产生的红利,中国的工业制造业能够在生产过剩以及由此造成的盈利能力危机的世界经济中获得较为丰厚的利润;现如今,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随着人口红利以及其它领域比较优势的丧失,盈利能力的危机如魔咒般地在中国的工业制造业中出现了,尤其是在缺乏技术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中国工业制造业凸显的问题再一次在经验上验证了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思想在逻辑上的一种自然延伸。
工业制造业是支撑一个国家运行和增长的基础,工业制造业的增长和繁荣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相反,工业制造业的危机、衰落,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停滞。同样,未强先衰也可能同时出现。因此,如何摆脱工业制造业的危机,如何避免中国经济的去工业化,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课题。尽管,一些宏观的经济政策、中观的产业政策以及企业的微观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危机,但这些政策无法解决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工业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长期过剩——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经济下行压力大,并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如何在全球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中,保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保障中国经济的繁荣,是一代经济学人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一代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群策群力,汇聚共识,共同为中国经济把脉。尤其是打破传统思维,从制度层面进行设计,并转变现有的发展方式,仍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所在。放眼世界,世界范围的制度转型和创新仍为世界经济走出阴霾的根本出路所在。
关于未来的研究展望
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去工业化是一个较新的主题,并且关于去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是否将工业制造业的萎缩界定为去工业化也存在较大的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今日之中国的工业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至少使我们无法回避这一研究主题。工业制造业的重要性是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为过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之兴衰在于工业制造业的兴衰。本书是对去工业化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而不是碎片化的研究,然而,正如笔者所言,去工业化是一个涉及面广的较新的研究主题,加之笔者有限的研究能力,所以,书中存在诸多的缺点和不足,尚待进一步改进,尤其是深入研究。笔者认为,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研究这一主题:
第一,继续深入挖掘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以及去工业化的相关影响。笔者认为,这一研究需具有整体性,并将其放置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历史嬗变中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
第二,回答工业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或者是广义的三次产业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均衡的比例,如果有,这一比例是什么,其动态特征是什么,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第三,如何认识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工业制造业困境,尤其是其背后的发生机制?笔者认为,大多数学者和观察家只看到工业制造业困境的表面现象,尚缺乏对目前困境的整体性且深入的认识,因此,必须深入挖掘。只有工业制造业困境的深层次原因被挖掘出来,才能回答现阶段萦绕着我们的许多问题,才能采取精准的对应策略。
第四,如果工业制造业的困境不可避免,也即发生了工业制造业危机,或去工业化,那么,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加以应对。鉴于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去工业化,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早熟去工业化”,具有极端复杂国情的中国,必须未雨绸缪,要有充分的预见性政策。
第五,工业化、去工业化与城镇化密切相关,因此,新型城镇化必须考虑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去工业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工业化、去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或者是“三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们必须重新且审慎地考虑,工业化、城镇化,或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历史经验的同时,中国更应关注其应有的特殊国情。一言以蔽之,要基于国情和现实重新思考工农业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