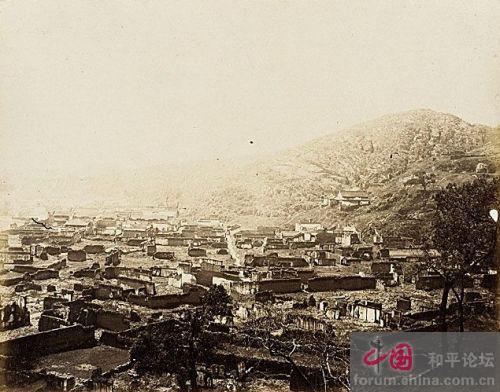村庄政治:理解农民集体上访的一种解释框架
——基于北镇的田野考察
陈 锋**
摘要:通过对一个乡镇的田野考察发现,在一些综合性集体上访中,“公开文本”所呈现的“维权”性质虽基本成立,但在“隐藏文本”层面则呈现农民谋利或者“出气”的实质诉求。从村庄内部视角来看,熟人社会的村庄结构使干群之间公与私的冲突交织连结,一些村民因为“衡平感”的丧失诱发“气”的产生、累积。在遵循“报”的行为逻辑下,上访成为“气”的宣泄途径或派系斗争的武器之一。因此,综合性集体上访是村庄政治运作的一部分,而非基于权利、利益或道义诉求的对抗政治。乡村内部政治冲突以各种“维权式上访”呈现,上升为地方政府乃至国家需要直面的问题,与村庄政治平衡的解体紧密相关。这是基层治理从“整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的意外产物,也是高压维稳政治背景下底层行为逻辑策略性调整的结果。
关键词:综合性集体上访 “气” 村庄政治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爆发,农民上访愈演愈烈,由此引发学界广泛关注。近十年来,学界关于农民上访的研究方兴未艾。农民上访自身经验的复杂性为上访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养分,使得对农民上访的分类、上访的性质以及分析框架均做出了多元且深入的探索,这有助于深刻理解转型时期农民上访的复杂性,这在政策实践和学术创新上具有双重意义。
由于经验基础差异和理论旨趣不同,农民上访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权利诉求—抗争政治”论、“利益博弈—非抗争政治”论和“道义伦理—底层政治”论。[1] “权利诉求—抗争政治”论最先提出,也成为对农民上访解释的主流框架,如“依法抗争”[2]“以法抗争”与“抗争性政治”[3]的提出。“权利诉求-抗争政治”论受西方抗争政治理论影响较大,其暗含的核心是作为弱者的农民一种有组织且有政治信仰的抗争,是社会中心的范式。这一范式多从社会对抗国家的视角出发,受意识形态影响过大。中国农民的上访更多是一种利益表达,而非政治性信仰的表达,在组织上更多通过草根动员,而非有组织化的动员。[4-5]中国农民对于“权利”的理解与西方有着根本不同,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将抗议诉求集中在抽象的公民权上,其抗争的目标往往聚焦于具体的权利要求。[6]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深度经验研究基础上提出“利益博弈—非抗争政治”论。相关研究发现,后税费时代农民的“维权型上访”大大降低,而无理上访、谋利型上访[7] 、求援型上访[8]等明显增多,农民的主要诉求是利益而非抽象的权利。取消农业税后,造成农民上访增多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方利益主体的失衡及农民上访甄别系统的瓦解。[9]乡村治权的弱化和分类治理能力的丧失也是信访治理的主要困境。[10]此外,在资源下乡、地方资源资本化背景下,利益流量巨大,但无法克服谋利型上访等机会主义博弈,这与国家推动基层从间接治理向直接治理,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紧密相关。 [11]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事务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分化的结果。[12]因此,当前农民上访主要是一种利益博弈,这并非抽象的基于权利诉求的政治问题,而是常态化的治理问题。
与“权利诉求—抗争政治”论和“利益博弈—非抗争政治”论不同,“道义伦理-底层政治”论主要受斯科特和印度底层政治理论的影响。在对中国农民上访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主要关注抗争策略,比如弱者的“韧武器”[13]、“依势博弈”[14]等概念的提出,另一些学者则提出应从“策略”向“伦理”转换,认为伦理视角在研究中国农民抗争研究中有独到的解释力。[15]应星运用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的“气”这一伦理性概念来阐释中国乡村社会的集体行动,“气”是由于基层政府对上访精英的惯有打压引发的反弹。[16]这一转向也将上访研究的焦点从现实性冲突向非现实性冲突转换,强调“被承认的政治” [17]。
应星引入伦理性的“气”这一视角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但在集体上访中,“气”的生成是否仅仅由于上访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抗?生发 “气”的运作机制与结构性因素又是什么?换言之,将“气”的引发停留在过程-事件之中,使得这一机制的产生可能具有偶然性,而对结构性的关注将有助于挖掘“出气式上访”的一些内在常规性机制。有研究发现,看似“维权”的上访,却是“出气”的一种手段,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农村阶层分化所引发的结构紧张与冲突。[18]这与应星所呈现的政府打压上访者所产生的“气”迥然不同。换言之,农民政治行为与政治伦理受到农村熟人社会中由人与人之间关联所形塑的村落结构的影响。2011年12月-2012年8月,笔者在在北镇累积调研超过180天,调研发现农民集体上访与特定社会结构背景下的村庄政治有着紧密的关联。基于此,本文通过北镇两个农民集体上访事件进行分析,关注农民上访的前史和后果,进而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探索农民集体上访中的“利益”、“气”与熟人社会的村庄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形成理解农民上访的一种新框架。
二、 综合性上访与基层治理困境
北镇现辖12个行政村,19个自然村,总户数9335户,总人口数3.25万人。近年北镇农民上访数量不断增加,信访治理工作压力也随之增大。针对农民上访的严峻形势,北镇先后成立信访办、综治办,调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主抓农村信访问题、群体性事件等社会矛盾问题,但并未扭转信访治理的局面,其表现之一便是集体上访越来越多。2007至2012年北镇共计发生农民集体上访17例(见表1)。
表1 北镇2007-2012农民集体上访性质统计表
|
类型 |
治理型 |
非治理型 |
合计 |
||||
|
维权型 |
求援型 |
谋利型 |
综合型(包含维权型、谋利型、出气型中的两种及两种以上) |
维权 |
求援 |
||
|
数量(例) |
3 |
2 |
4 |
6 |
1 |
1 |
17 |
|
比例(%) |
17.65 |
11.76 |
23.52 |
35.29 |
11.76 |
100 |
|
根据农民上访的性质,可将其划分为治理型上访与非治理型上访两大类,治理型上访主要指由于乡村治理能力弱化或者基层治理失范而引发的农民集体上访。非治理性上访主要指那些诉求内容超过基层政府职责与权限,乡村两级无法解决或者无力解决的上访。具体而言,治理型上访又可以分为维权型、求援型、谋利型、出气型等上访形式。维权型上访主要指农民的权益受到乡村组织一定的侵害,而向政府部门反映、揭发基层组织违反国家政策、制度问题,并要求保护他们利益的集体上访,典型如村级财务问题上访。求援型上访指农民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碰到困难或者纠纷,通过上访向基层政府求助,申请政府解决或者协助其解决问题,这类上访诉求通常是乡村两级组织职责权限内的事情。谋利型上访主要指农民提出超出其合理范围或本不合理的诉求,具有较强的谋利、自利动机,以上访来获取物质利益和其他利益的行为。出气型上访指的是由于一些事件使农民主观上感受到人格受损,进而在心中蓄积“气”,为了获得承认并找回内心的“衡平感”而通过上访的形式进行表达。出气型上访在当前的信访制度框架内无法寻求其合理的依据,通常夹杂在维权型上访、谋利型上访之中,因此本研究将维权型、谋利型和出气型两种以上性质的上访归结为综合性上访。2007-2012年,农民的综合型集体上访发生6例,占35.29%。这类上访成因复杂,成为当前基层政府面临的治理难题,为此,本文主要关注这一类型的上访,从中剥离出农民上访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
三、 农民集体上访的“公开文本”
在农民的集体上访中,农民通过文字或口头表达呈现出自己的上访诉求即为公开的文本,而未在公开的上访中明确说明的其他诉求、话语和实践则是隐藏的文本。通常,农民自我宣称的“公开文本”中,“维权”占据主流,构成其集体上访合法性的基础。以“维权”作为合法性,既能凝聚集体上访参与者的共识,增强集体行动力和可持续性,又能借此获得上级政府的关注与同情,进而求得上级政府的积极介入。
案例1 2008年11月至2012年8月,辽东北镇窑村谭春明组织了村里的8位老人到F市市委、市政府、市纪检、市信访局进行了超过10次以上集体上访。上访事项主要涉及村主任何海的村级财务问题,包括款项去向不明、一些款项没有上账、村干部贪污以及村砖窑厂乱占土地、林木超伐等问题共计20项。为此,F市信访局、F市纪检、北镇经管站、水利站、林业站等专门成立专项调查组对其逐一复核,并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意见。谭春明等人所信访的问题部分属实,村主任何海存在一些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北镇人民政府对村主任何海处以党内警告处分,其他一些事项如村集体的砖窑厂多占土地等则由F市国土局对其进行处理。谭春明等人对北镇政府的处理意见书、F市纪检委出具的函、F市信访局出具的复查意见书却不满意,整个上访持续三年多的时间,仍未息访。
案例2 2012年4月5日,北镇东村村民集体上访,声势浩大。大约50人聚集在乡镇书记的办公室,他们举报村干部从2011年12月起将村庄的林木滥砍滥伐两三百亩。村民要求处置现有村干部,并已列出他们自己推选的新干部名单。同时说明所得费用的去向。上访的群众中,妇女占据了三分之二。一些上访代表被安排到北镇党委书记办公室反映具体问题,一些人被安置在会议室,一些人在走廊上大声喧闹,情绪有些激动。另外,上访者手持摄像机,拍摄了整个上访的全过程。为此,北镇的经管站、林业站以及丰市的森林公安全面介入调查。最终,东村村书记引咎辞职,负责砍伐的相关人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案例1、2中,两例集体上访,农民以“维权”为由进行上访是基本成立的。村民集体上访针对的都是村干部,理由均是村干部存在违规违法行为,例如财务违规、多占土地问题、滥砍滥伐等行为。不过,上访村民罗列的情况并非完全属实,比如案例1中村主任存在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在“村财镇管”的背景下,一些款项没有上账、自存自取即是违规,但如贪污等其他财务问题经过多方审计并不成立。但村干部的违规违法行为理应受到相应制裁,两例集体上访在“公开文本”中属于“维权”行为。
然而,案例1中谭春明等人的集体上访历时三年多仍未平息,对北镇政府的处理意见书、F市纪检委出具的函、F市信访局出具的复查意见书均不满意。如果仅仅“维权”,谭春明等人何以在案件处理完毕后仍未平息?案例2东村村民到北镇进行集体上访时,一些上访者并不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委,参加上访却能获得上访组织者给予的每天100元补贴。上访精英又何以需要花钱雇人上访?这些上访的民众是否存有其他隐藏的诉求?换言之,农民的集体上访的“公开文本”背后可能存在一套“隐藏的文本”。
四、 农民集体上访的“隐藏文本”
斯科特认为“公开文本”并不表现从属者的真正观念,它可能只是一种策略。“隐藏文本”则是一种隐匿在后台的话语和实践,从而避开掌权者的监视,底层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独立而且统一的。[19]
在案例1中,窑村的村主任何海一直是上访者的矛头指向。谭春明原是窑村的老会计,2005年退休后被安排到村办企业砖窑厂担任副厂长兼会计。2008年9月,村主任何海发现他存在账目作假、吃回扣和对自己家属特殊照顾的现象,便召开班子会议将谭春明辞退,双方为此发生激烈争吵。然而,谭春明作为村里的老会计,对村庄账目的问题十分了解,为了动员群众,谭春明夸大一些问题,如林改资金的去向和使用的问题。上访的初始阶段,村民对这位老会计较为信任,也较为支持。同时,他动员了7位老人一同参与,并承诺一旦上访成功,便为他们发放误工补贴。这7名上访者中,其中3人是被动员起来的,其余4人均与村主任有一些过节。由此可见,在“公开文本”中,谭春明等人的集体上访可定性为维权行为,绝大多数的上访者并非为了获取物质利益,甚至在客观上对村干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纠正,保护了村集体利益。但是,他们上访的真正动机却是“出气”。各种个人之间、公私之间的恩怨汇集起来,成为集体上访的主要原因。对他们而言,上访的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访本身能够表达、宣泄他们的情绪,同时能给“对手”制造麻烦。“只要我们还在上访,他们就不得安稳”,这或许最能诠释谭春明等人不断上访的根本目的。
与案例1不同,案例2中农民上访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动员范围也较广。在“公开文本”中,两位上访精英为举报村干部滥砍滥伐而不惜重金组织民众集体上访。他们是上一届村庄选举的落选者,曾花费数万元进行贿选却未成功,也因此对现任村干部不满。他们组织集体上访的主要目的是废黜村干部,并自拟了一份“新村干部名单”提交给镇政府。在这份名单中,两位上访精英分别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为了造势,他们给予每天100元补助以动员其他村民上访。在上访群众中,一些农民确因林木被砍伐而气愤,一些村民是在利益补助的刺激下参加上访。有一位较为活跃的专业上访户张九,经常以上访作为威胁谋取小恩小利,他曾向东村周主任提出8万元的息访条件,并表示可以使其他上访者息访。还有三名上访者则是村庄中林木偷盗者,曾被村干部发现、举报,为此结下仇恨。由此观之,东村的集体上访,有落选者的“出气”,也有上访专业户和部分村民的谋利,还有少数农民的维权。但从上访的组织、策划而言,这是选举之前的权力斗争,是村庄派性政治的结果。上访精英借助上访,既出“落选”之气,又能以此赢得民意,以便在新一届选举中翻身。村书记的引咎辞职,实现了他们的部分目标。事实上,当前农村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之一便是选举引发的派性斗争,不少农民上访的组织者就是老干部和想当村干部的村民。集体上访虽在客观上对当权者形成一定的制衡,但又使之陷入派系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造成村庄公共治理陷入亚瘫痪状态。尽管上级政府会对集体上访反映的问题进行查处,却无法触及反对派与村干部之间的根本矛盾。
综上,在综合性集体上访中,“公开文本”所呈现“维权”的性质虽然成立,但维权并不构成集体上访者的全部动机,甚至并非主要动机。剥离“公开文本”中的维权或者利益诉求,农民更因日常生活政治或者村庄派系政治而将上访作为“气”的宣泄途径或斗争武器。在这一意义上,一些农民的集体上访是村庄政治运作的一部分,而基于权利、利益或道义诉求的对抗政治。
五、 村庄政治视野下的农民上访
“权利诉求—抗争政治”论、“利益博弈—非抗争政治”论和“道义伦理—底层政治”论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农民上访的性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基于不同上访经验类型的解读,也可能由于理论旨趣不同,使其仅能呈现农民上访的一个面向。正如霍耐特所言:“一种社会冲突在什么程度上服从利益追求的逻辑,又在什么程度上服从道德反应的逻辑,这永远是个经验问题”。[17](p38)本研究从综合性上访中挖掘农民集体上访的多维面向,并借用斯科特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进行分析,揭示农民上访的实质。
(一) “衡平感”丧失与熟人社会中“报”的逻辑
熟人社会中的政治,既包含日常生活互动、日常治理中的政治,也包含村庄权力斗争中的派系政治。乡村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几代人相守在一个村落,人与人之间有着紧密且可持续的互动。在个人之间、公与私之间以及权力斗争中的互动中,冲突便是村庄政治社会的常态。但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中,这些利益或非利益冲突通常难以一次性了结,而可能形成“气”的累积。因此,村庄这一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恰恰提供了“气”的生发环境。
通常,村民之间发生摩擦或较小的利益冲突,为和谐共处可能忍气吞声、克己复礼。但是,一旦超越农民的心理底线,则可能在某一时间累积性、整体性地爆发,正所谓“人争一口气,树争一张皮”。“常识性正义衡平感”[20]的丧失诱发“气”的产生。这种“衡平感”是当事人的一种主观感受,一种顾及人的全部与整体的观念,而不仅是就事说事的观念。也即,“中国人具有不把争议的标的孤立起来而将对立的双方,有时进而涉及到周围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和总体考察的倾向;而且中国人还喜欢相对的思维方式,倾向于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侧都多少分配和承受一点损失和痛苦中找出均衡点来,等等”。[20]综合性上访中的“出气”即是找回“衡平感”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上访“维权”是“虚”,“出气”为实。
“气”在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内涵,但纯粹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则脱离经验本身。从农民的“出气”式上访来看,他们共同遵循了熟人社会中“报”的运作逻辑。“报”的逻辑,包括“报恩”和“报仇”,均是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但是,“报”由封闭性结构引起,这种结构正是与中国的社会结构相吻合的,其根本基础正是来源于村落生活的相对封闭性和世代性。[21]因此,在村庄的熟人社会中,出气式上访所蕴含的“报”逻辑,首先作为一种情绪性的宣泄表达以寻求内心的衡平感,这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以及日常治理的互动中所引发的冲突。此外,“报”还意味着“出气人”要在乡土社会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村落权力的派系斗争中,许多组织农民上访的精英便是如此。
因此,从村落的社会结构,或者从熟人社会的村庄政治这一视角更容易理解“气”的产生、累积和爆发的过程和机制。村庄熟人社会中紧密的互动使各种利益或情感冲突成为村庄社会的常态,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则是“气”得以累积的社会基础,而“气”的爆发以上访的形式出现则在于村干部的特殊身份——既是作为国家代理人,又是村民一份子,使其公私之间的矛盾交错联结,上访这一公共路径成为村民对其进行反制或报复的手段。
(二)村庄政治平衡的解体与维稳政治下的底层逻辑
村落中基于公私之间或者派系之间的冲突是历史常态,也是村庄政治的基本生态。村民为了获得“衡平感”会遵照“报”的逻辑行事,但是这些冲突在地方性共识的框架内多以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方式解决。当前乡村冲突所累积的“气”的爆发却表现为各种“维权式上访”,并日益成为农民惯用的手段,上升为地方政府乃至国家需要直面的常规问题。因此,村庄政治作为理解农民集体上访的一个视角,还需从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关系之间的变化中进一步理解。
所谓村庄政治主要指村庄内部展开的政治,是村庄内部为达成利益再分配而进行的协商、博弈、斗争与妥协,它是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的过程,进而形成各方面力量相对平衡并维持村庄秩序的结果。[36]农村税费改革前,村庄政治的核心主要是农业税费征收和计划生育。在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的连带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也将其需履行的义务与应该享受的权利捆绑连带,并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进而实现村庄秩序的基本平衡。[22]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的生育观念发生重大转变,农村税费取消,国家开始输入大量资源反哺农村,“争资跑项”和“综治维稳”成为新时期的乡村中心工作。村庄政治的核心是国家资源输入和地方资源资本化背景下资源或利益的再分配,一些地区的乡村社会形成巨大的“利益场”。为了掌握资源的分配权以及实现利益最大化,村庄选举愈加激烈,干部与(老)干部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均形成较大的利益冲突。
伴随国家治理模式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法治化、规范化、技术化和标准化成为行政建设和监督的核心议题。[23]乡村两级组织在权力运作愈加要求依法行政、讲究程序、讲究民主、按制度办事,实行协商治理。然而,随着农民从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在从整体支配转向协商治理的过程中公共规则的落实缺乏强制性作为保障,而“连带式制衡”机制运作的制度和资源基础丧失,村庄政治的内部平衡解体,基层治理陷入重重困境。
与此同时,在高压维稳政治背景下,各级政府强令要求基层组织严格控制农民上访,并以此作为考核基层组织的指标。如此一来,必然诱发基层组织花钱买平安甚至不惜动用灰黑势力进行摆平的策略主义行为。动用灰黑势力使得一些“上访户”或“钉子户”因为恐惧而暂时妥协,但也因此激起村民更大的“怨气”。高压的维稳体制对基层组织进行监督和施压,基层组织遵照“不出事”的行为逻辑进行摆平,也恰恰给予农民机会主义博弈的政治空间。农民的底层政治逻辑演变为——“你越是怕上访,我就越上访,你越怕越级上访,我就越是要通过越级上访再给你施压”。换言之,农民在高压的维稳体制中反而占据一定的有利位置,农民可以通过上访倒逼基层组织介入权益的保护、矛盾纠纷的调解或公共品的供给,这也是后税费时代农民上访增多的重要原因。这一制度也造成了一个意外后果:一些农民恰恰深谙乡村组织“怕出事”的心理,打着“维权”的幌子,通过上访甚至集体上访实现自身的非正当利益,或者将其作为“出气”的手段抑或作为村庄派系政治斗争的武器。旨在消除不稳定因素的维稳工作,实际上已经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形成“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25]
六、 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在急剧转型,随之带来的社会冲突也在不断加剧,其重要表现之一便是农民的集体上访不断增多。通过对一个乡镇综合性集体上访的田野考察发现,在“公开文本”层面呈现出农民维权的面向,而在“隐藏的文本”层面则呈现出农民谋利或者“出气”的实质诉求。更深层次而言,在一些综合性上访中,“公开文本”所呈现的“维权”性质虽基本成立,但维权并不构成集体上访的全部动机,甚至不是主要动机,农民更因日常生活政治或者村庄派系政治而将上访作为“气”的宣泄途径或斗争武器。从村庄内部视角出发可以发现,综合性的集体上访是村庄政治运作的一部分,而非简单意义上的基于权利、利益或道义诉求的对抗政治。
农民集体上访中的“维权”为虚、“出气”为实的原因首先在于熟人社会的村庄结构使得干群之间公与私的冲突交织连结,一些村民因为“衡平感”的丧失诱发“气”产生并遵循“报”的行为逻辑,上访成为上访者情绪性的宣泄表达以及要在乡土社会中重新找到自己位置的手段之一。当然,村落中基于公私之间或者派系之间的冲突是村庄政治的历史常态,并多在地方性共识的框架内以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方式解决。然而,当前乡村社会冲突所累积并爆发的“气”却以各种“维权式上访”呈现,并日益成为农民惯用的一种的手段,上升为地方政府乃至国家需要直面的问题,则与村庄内部政治平衡的解体紧密相关。这是基层治理从“整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的意外产物,也是高压维稳政治背景下底层行为逻辑策略性调整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从村庄政治的视角出发意在提出一个理解农民集体上访的解释框架,这并非是对既有上访研究解释框架的否定,鉴于经验本身的复杂性,既有研究对上访的复杂性和层次性仍缺乏进一步揭示。本研究所揭示的集体上访的层次性和复杂性也仅是上访类型之一,并意在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基于本研究的经验发现,在改革高压的信访制度之外,重建村庄政治,使村庄内部具有为达成利益再分配而进行的协商、博弈、斗争与妥协的能力,或是维持村庄秩序平衡减少农民上访的重要方向。首先,严格规范村庄的选举政治,防止派系斗争激化。当前,因选举而诱发的派系斗争不仅造成村庄社会的内部关系撕裂,而且导致乡村治理陷入“故意制造麻烦”的困境。因此,严厉打击贿选、胁选等行为,对候选人进行严格审查,加强对现任村干部队伍的教育与培训,注重村干部后备队伍的培养,使村干部的素质能够进一步提高,并且能够在选举中较为平稳的过渡和更替。其次,关注农民的生活政治,预防公私矛盾交错。乡村治理嵌入在乡土社会之中,农村人讲究人情、面子,并非完全遵照法律、制度的逻辑。因此,基层组织应关注农民的日常生活,尤其要关心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维护他们的尊严,防止将日常生活矛盾转化为基层治理矛盾。最后,建立村庄社会的“分配性政治”,以资源联结构建农民与基层组织相互关联又相互制衡的关系。对发达地区农村而言,村庄的内生资源和利益较为密集,村庄贫富分化较大,底层群体往往难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利益诉求,进而产生较大的怨气。因此,一方面要避免富人垄断政治,造成权力滥用和贪污腐败,加强对村级组织的监督,一些沿海地区目通过推行“晒权力清单”的形式对于构建农村小微权力监督规范体系便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另一方面,应增强基层政治的开放性,让普通农民有机会参与到村庄政治中,尤其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能享受公平参与村集体的利益分配,这便需要真正做好村民代表和村干部的选举工作,有效落实村民自治制度。对利益较为稀薄的农村地区,由于集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乡村社会内部面临治理资源匮乏的困境,资源下乡的背景则构成当前乡村治理的契机。在资源输入与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应让普通村民参与进来充分表达公共品供给的需求,并参与对资源的分配和项目实施的监督。如此一来,通过资源分配的各个环节可以有效建立村民与村级组织之间实质性利益联结纽带,也有助于在民主选举之外,真正培育村民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意识,夯实村民自治,进而增强乡村社会协商治理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陈锋.从抗争政治、底层政治到非抗争政治——农民上访研究视角的检视、反思与拓展[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2]李连江,欧博文. 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C].吴国光编.九七效应:香港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
[3]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2).
[5]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的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5).
[6]裴宜理.中国人的“权利”概念(下)[J].国外理论动态,2008,(3).
[7]田先红.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1995-200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8]焦产权.政权悬浮与市场困局:一种农民上访行为的解释框架[J].开放时代,2010,( 6).
[9]贺雪峰.国家与农民的三层分析——以农民上访为问题意识之来源[J].天津社会科学,2011,(4).
[10]陈柏峰.农民上访的分类治理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2,(1).
[11]陈锋.从整体支配到协商治理:乡村治理转型及其困境——基于北镇“钉子户”治理的历史考察[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12]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3]折晓叶.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J].社会学研究,2008,(3).
[14]董海军.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5]吴长青.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J].社会,2010,(2).
[16]应星.“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社会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7]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8]陈锋、袁松.富人治村下的农民上访:维权还是出气?[J].战略与管理,2010,(3).
[19]Scort,James C.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20]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的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C].王亚新译,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1]翟学伟.报的运作方位[J].社会学研究,2007,(1).
[22]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关于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初步讨论[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
[23]陈锋.连带式制衡: 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J].社会,2012,(1 ).
[24]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25]清华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J].学习月刊, 20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