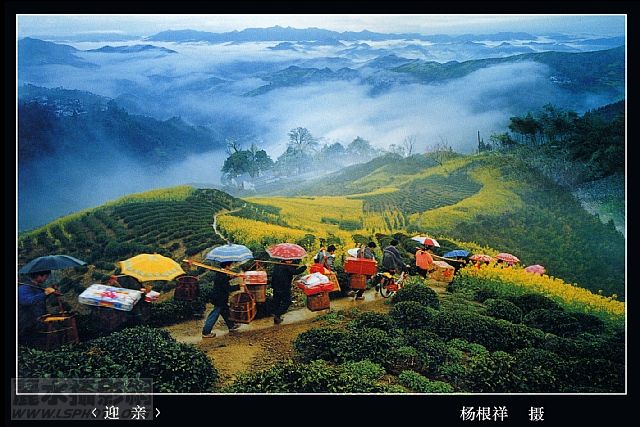社会性小农:小农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基于江汉平原农业发展的启示
杜鹏
内容提要:由于农作参差期、土地细碎化和农作环节的关联性,小农生产关系呈现出强烈的社会性。社会性小农是小农经济运行的真实主体,它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合理配置资源和有效安排生产,从而尽可能克服小农家庭生产的局限性。社会性小农的弹性意味着不仅可以降低村社生产体系的治理成本,而且可以有效对接社会化生产服务体系,为资本、技术等要素与土地的结合创造条件。社会性小农奠定了小农经济持续发展和适应性变迁的基础,维持了小农经济的稳定性。
关键词:社会性小农;小农经济;发展;适应性变迁
一、引言
“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必须长期面对的现实。从经营规模看,中国农民经济的本质仍然是小农经济,但它实际上已经嵌入高度开放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体系。小农经济的命运和走向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主要表现为两条道路之争:小农经济的资本主义转型抑或小农经济的内在发展。
主流学界和政府部门主要聚焦于改造和消灭小农经济。走出小农经济的陷阱(曹东勃,2009),实现规模经营,被认为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种观点假定小农生产的家庭化取向,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关于小农经济分散性的认识。分散的小农家庭农场因为难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被资本主义改造(马克思,2004)。农业生产主体因而成为小农经济转型的焦点,并表现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导向。农业转型在很大意义上转换为农业治理转型(冯小,2015),从而忽视了现代化过程中小农经济在生产关系层面的自我调适以及自发性农业现代化的可能路径。
恰亚诺夫(1996)强调了小农家庭的内在运行逻辑,认为小农经济能以其农民生产方式抵御资本主义渗透,但他忽视了小农家庭之间的生产关系以及小农经济内在发展的可能性。生产关系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劳动过程中进行经济协作的结果。问题是,既有研究将“生产关系”主要理解为小农与不同生产体系(村社生产体系和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关系,农户在生产实践和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关系并没有受到充分关注。因此,农业生产关系有两个维度,即小农与“村社体系/社会体系”的关系以及小农户之间的关系,二者分别构成生产关系的制度维度和实践维度。
农业生产不仅是一种要素配合的经济过程,而且也是关系协调的社会过程。由于对小农生产关系的实践之维缺乏足够重视,小农生产结构仍然是一个“黑箱”,其内在社会机制有待于进一步阐明。事实上,社会性小农而非孤立的小农家庭才是小农经济运行的真实主体,并且构成了小农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的发展表现为小农生产中的机械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和资本要素比重的提升。农业机械化并未受到小农分散经营的的阻碍,反而进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快速发展时期(侯方安,2008),从而构造了小农经济的现代图景。本文试图基于社会学视角,揭示小农经济内部孕育的自发秩序和适应能力,从而阐释小农经济的发展逻辑。
作为中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和水稻重要产区,江汉平原的农业发展历程在一般农业型地区颇具有代表性。分田到户以来,当地小农经济经历了一个朝向现代化的适应性变迁过程。以笔者调研所在沙洋县为例,当地农业机械化水平综合比率已经达到73%,小农经济与机械化达到较高的结合度。江汉平原小农经济发展的鲜活经验有力地反驳了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转型的必然性,呈现了小农经济内在发展的可能路径。
笔者于2015年4月在在湖北省沙洋县黄村开展了为期20天田野调研。调研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主要关注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生产策略、农作模式、互助合作以及农业变迁等内容。黄村地处于江汉平原腹地,拥有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该村共有土地面积约3500亩,1065人,250户。人均土地面积达到3亩,户均土地超过10亩。虽然当地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始终面临一些难题,但是,面对不同的的限制性条件和内外部环境,社会性小农以不同的行动逻辑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的有效安排,从而尽可能克服小农家庭生产的局限性,降低小农与村社生产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对接的成本。
二、小农生产结构的基本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有其特定规律,主要表现为时间对空间的规定性。农民遵循农时安排生产,小农生产因而具有较大的时间伸缩性。大集体时代农业生产的全面组织化压缩了农业生产的伸缩性,导致农业生产的内卷化。分田到户以来,家庭重新成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之下,村集体为农业生产提供公共品服务,形成农业生产的村社服务体系。农业生产本身的逻辑再次居于主导地位,且形塑着特定的时空架构之下农户间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秩序。
(一)农作的参差期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作物生产过程虽有一定的周期,但是农户之间的农时却并不必然保持一致,可能表现为一种参差错落的状态。农户之间的农作日历的参差性有时间上的限度,继而规定了农作各个环节的劳力配置。这段时间可称为“农作参差期”(费孝通,张之毅,2006)。农作参差期的长短主要依据农作物的性质和气候条件而定。农作参差期赋予了小农生产以时间弹性,这为小农之间的生产合作留下了空间。利用农作参差期,有利于缓解劳动力的季节性供给不足,优化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社会最优状态。例如在水稻生产的插秧和收割环节,在农作参差期内,农户之间通过“换工”可实现劳动力的均匀配置与充分利用。农作参差期界定了农户之间的协作空间和协作策略,进而影响着农户的全年生产决策。例如,在不种植油菜的情况下,5月1日之后就可以开始插秧,6月1日之前插完即可;但若种植油菜,油菜收割在5月10日左右,而小麦收割则在5月20日左右,农作参差期则分别为20天或者10天。农作参差期除受自然条件和生物条件影响之外,也受到社会因素、技术条件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稀缺、机械化水平提高等变化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快节奏化,农作参差期不断受到压缩,这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农户的生产安排与生产策略。
(二)农地的细碎化
土地的零碎分割是中国目前小农生产的基础性条件。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质量和基础设施的差异,分田到户时普遍采取了以土地等级划分为基础的平均主义的承包方式。土地面积较小,且土地不连片,农户之间的土地呈插花分布,奠定了小农生产的基本格局。据黄村2005年的统计数据,该村土地块数共3041块,即人均3块,块均7分左右。对土地细碎化的效益评估,不应忽视土地的这种空间安排格局是农户在当时特定生产条件之下做出的一种理性和自愿选择。农民之所以普遍追求以土地为基准的平均主义,实际上是因为土地生产率而非劳动生产率主导着农民的理性观。在当时条件下,土地生产率主要受自然条件(水、土、肥)的影响,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并不会计较因田地的细碎分散而付出的额外劳动力。农地的细碎化对小农生产关系产生了微妙和重要影响:
首先,在集体水利条件下,农田细碎分散化可以分散劳动时间的集中程度,优化农业劳动在整个生产过程的时间分布,从而实现劳动力的有效利用。农民认为:“田分散,(我)有(的田在)上游(有的田在)下游,有先有后!要不然,我都在上面,上面在栽,下面就只好巴望着!”
其次,以户为基础的农地分散以及户与户之间的插花分布,导致农户生产过程中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制衡,弱化了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自主性,为了克服农业生产中的“负外部性”,就产生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协作要求。这尤其表现在农民对“过水”和“过田”的体会上:“你(机械)走我的田。我走你的田。互相拉扯,都无所谓。抽水也是一样。你控制我,我控制你。你还走不走别人的!?人都有个利己的思想……”
但是,随着农作参差期逐渐压缩,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和农村生产服务体系的弱化逐渐导致土地细碎的问题化。土地细碎的空间格局日益成为小农生产的主导性限制因素,形成了空间对时间的规定性。
(三)农作环节的关联性
小农生产在特定的时空架构之中展开,其各个环节紧密相连,形成一个有机系统。农作环节的关联性不仅指农作物内在各个生产环节的相关性,而且也指轮作模式下不同农作物之间的生产环节关联性。例如,水稻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泡种——育秧——耕整——移栽(插秧)——田间管理——收割,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农作方式和生长效率的改变均会逐渐传导至其他环节。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逻辑实际上是从一个点突破,而逐渐传导至其他农作环节,最终形成一个新的均衡系统。农作环节的关联性意味着小农生产结构的内在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为小农生产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基础。
表1 机械化及轻简便技术的推广(以水稻为例)
|
|
耕整 |
播种 |
收割 |
|
第一阶段 |
牛 |
水秧移栽 |
人工收割,牛碾,人工扬 |
|
第二阶段 |
手扶拖拉机 |
抛秧 |
人工收割,脱粒机 |
|
第三阶段 |
旋耕机 |
机插秧 |
联合收割机 |
不同的农作方式有不同的效率,进而决定了对于单位面积土地大小的需求程度。例如,在第一阶段,用牛耕田,一个人一天不到1亩,而用拖拉机,则一个人一天可以达到4~5亩左右,用大型的旋耕机,一天可达10多亩。但是,如果插秧的效率没有跟上,耕整出来的田不能及时插秧,田块渐渐板结,同样会影响效率。再如,在早期农作效率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秧苗在最佳育秧期之内移栽,一些土地面积较大的农户往往需要分批育秧,从而留出足够的缓冲时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逐渐普及和收割效率提升,错开水稻生长期的必要性就不大了。农作环节的关联性,使得机械化的进入引发了农业生产方式变迁的连环效应和倒逼机制,并逐步重构了小农生产过程的时间节奏,压缩了农作参差期,小农生产结构渐趋平面化。
三、社会性小农的内涵与表现
(一)社会性小农的内涵
徐勇(2006)认为当前农民生产、生活和交往都被卷入“社会化”大分工网络,基于这一特性,他提出了“社会化小农”概念。“社会化小农”对于透视当前农户的行为模式无疑是富有启发的。不过,此概念关注的主要是小农与社会化体系之间的关联,着眼于社会转型背景下小农发展的阶段性定位,即将社会化小农视为传统小农向理性小农过渡的中间阶段。与徐勇不同的是,本文提出的“社会性小农”主要指涉更为微观层次的农户间生产关系。“社会化小农”虽然也强调了小农生产要素配置的社会化,但主要强调个体的小农与社会化体系之间的嵌入关系。因此,社会化小农对农业生产关系的揭示仍然局限于笔者前文提及的“小农—社会化”体系的层次,未能进入小农生产结构。基于此,社会性小农的概念将有助于重新审视小农生产的运行机制,同时也构成理解“社会化小农”及其行为逻辑的基础。
社会性小农是笔者立足于小农生产结构而提出的概念。社会性小农强调小农生产的社会性,具体指的是小农生产并非仅仅依托家庭而展开,在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出于生产要素最优化配置和生产服务体系有效对接的需要,农户之间通过互助协作,具有形成自发秩序的动力和潜力。具体来讲,农作参差期为小农的生产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土地细碎化为小农的生产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农作环节的关联性则为小农生产方式的变迁注入了可能性。因此,社会性小农植根于小农生产结构,并借助村庄“熟人社会”(宋丽娜,2009)中的关系运作实践而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性小农是小农经济运行的真实主体,它打破了既往研究对小农家庭生产的分散性偏见,从农业生产内部揭示了小农生产的运行逻辑和展开方式。社会性小农是村社体系和社会化体系之下的生产主体,且主要以微观、零碎和自发的形态存在。它既相对独立于外部体系,同时又构成分散的小农对接生产体系的基础。依托社会性小农,农业生产关系形成“小农”——“社会性小农”——“生产服务体系”的三层结构。
(二)社会性小农的表现
(1)内向互助
内向互助实际上延续了传统小农经济的村社互助传统,体现了在小农在要素稀缺条件下资源利用最大化的生产策略(刘显利,2013)。具体来讲,内向互助主要基于农作参差期的时间架构展开。社会性小农内向互助的实践形态凸显了小农生产系统的有机性和整体性。它依托熟人社会的人情运作而展开,体现了村社本位的生产逻辑。农业生产过程因而表现为比较彻底的遵循自然节律的过程。在这种模式下,家庭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刚性通过社会性小农的互助合作形态化解,而生产要素的不足通过村社内部小农户之间的共有和共享的方式得以缓解,同时也增加了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比较典型的经验是农户共同养牛、插秧和收割过程中的换工等。小农家庭并不过分追求自主性和独立性,反而通过在农作参差期中对农户关系的协调,促进了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2)外向协作
小农生产的稳健运行需要特定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与之相配套。外向协作涉及小农户与服务体系的对接。与内向互助不同,外向协作建立在小农户一致行动的基础上。外向协作主要基于农地细碎化的土地空间格局,其实质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协调缓解土地插花分布的负面影响。例如,在村社体系的集体水利供给过程中,同一个水系农户需要在冬播作物的种植结构选择上协调一致,否则,就可能影响生产效率,造成生产纠纷,也无形之中增加了“赶季节”的劳力配置压力。在机械化服务体系之下,由于机械化对基础设施和作业规模的要求,机械化表现出以“相邻成片”的农田为服务对象的偏好。为了对接机械化服务体系,土地相邻成片的农户需要在育秧、耕整、插秧、收割等农作环节协调时间进度以保持一致,这就为“田友”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农作时间的协调一致既可以化解“过水”和“过路”造成的干扰,还可以有效的转化为生产服务的规模效应,提高农户与机械化市场的谈判能力。
(三)社会性小农的弹性
社会性小农的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社会性小农通过自发的社会性合作的方式应对资源稀缺、资源过剩、资源对接的能力,这是社会性小农的转化能力,从而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将优势条件充分发挥;其次,则是社会性小农伴随着农业约束性条件的改变而逐渐调整自身的能力。因此,社会性小农的弹性既具有较强的结构适应性,也具有较强的变迁适应性。
社会性小农是一个历史范畴,其表现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伴随着社会化生产体系对共时性协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小农经济从村社生产体系向社会化生产体系的演变实际上是一个内向互助逐渐弱化和外向协作逐渐增强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向互助逐渐服务于外向协作的过程。由此,社会性小农适应了农业生产关系转型。社会性小农的弹性是理解小农经济发展的关键。同时也要看到,社会性小农的弹性也具有限度,其限度植根于社会性小农所依托的熟人社会关系的承载能力。随着农作参差期的压缩和生产合作密度加大,熟人社会关系逐渐难以承载和消化生产过程中因日益密集的协作而产生的外部性,这就产生了农地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以推动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四、社会性小农的微观运行机制
社会性小农是农户基于共同的小农生产结构而形成的一种小农生产主体,社会性小农的能动性适应是理解中国小农经济发展的基础。笔者将分田到户以来的小农经济分为两个阶段,并分别考察不同的生产服务体系下社会性小农的运行机制。第一阶段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形成的“村社体系+社会性小农”的模式,村集体为小农生产提供诸如水利等农业生产服务;第二阶段是开放性生产系统下“社会化服务体系+社会性小农”的模式,农业服务体系走向市场化。社会性小农由此体现出对不同农业体系的适应能力和适应方式,构成小农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一)“村社体系+社会性小农”模式
“组织起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视角,强调村组集体对分散小农的整合作用,从而解决一家一户难以解决或解决起来成本过高的问题,在稻作区以农田水利最为典型。一般认为,村组集体的介入可以有效克服农业生产中的外部性困扰,而“村社体系+小农家庭”的统分结合模式也足以调动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如果离开了社会性小农在村社层面的自发资源配置和协调的能力,集体组织的有效性就会缺少微观基础。从农业生产的视角来看,组织化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集体水利体系与不同受益主体生产安排的协调程度,后者又取决于农户在多大程度上有效配置稀缺资源和充分利用过剩资源。
具体来看,如果共处一个微型水系的农户农作时间不一致,下游农户需要抽水,但上游的田因为某些原因不能要水,例如,上游已经关水撒肥,或者上游作物正值稻谷“扬花”的时候,诸如此类的情况最终可能导致延误农时而减产,或者因为强行过水而引发冲突和矛盾,从而产生较高的协商成本和经济成本。还要注意的是,在一片水系之内,由于各家田块大小、面积、家庭劳动力情况(数量和质量)并不相同,在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发育的情况下,内向的换工互助是一种调试农户之间生产节奏的必要方式,从而为农户对接以水利为主要内容的集体生产服务提供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这个阶段,外向协作实际上主要通过内向互助的方式实现。在农民看来,“这一片的几户人,如果水已经放过来了,就会整这一片的田,该哪家插秧了,小组里的人,还有那些老表们,就会过来帮忙。”这也意味着,换工主要是在不同水系的农户之间进行的,并最终服务于水利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事实上,分田到户以来,小农家庭的生产自主性始终与集体组织的统一性之间存在张力。集体服务供给的有效性被简化为村庄治理的有效性:村组集体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农业生产服务中的“搭便车”问题,关涉到的集体组织的效率与功能(贺雪峰,郭亮,2010)。治理的维度当然非常重要,否则,收不上来共同生产费,集体的水利供给难以维系。但是,仅仅从自上而下的视角理解小农经济的运行效率并不充分。农户之间的自发合作和生产关系的自发协调有助于化解村集体与小农之间的张力。因此,社会性小农的视角展现了小农经济的社会性运行机制的相对独立性,正是其内在逻辑的相对独立性,使得小农可以在不依赖村社体系的情况下直接对接社会化服务体系,村社体系的崩解并没有阻断小农经济的发展进程。
(二)“社会化体系+社会性小农”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打工潮”导致江汉平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在村农民通过流转外出务工者的土地而扩大耕作面积,农业生产从劳力过剩向劳力不足转变。同时,随着农民收入提高以及“工业反哺农业”持续推进,机械化逐渐得到推广,如表1所示,收割机经历了由农户自购的小型手扶拖拉机到大型旋耕机、收割机的变迁,插秧机也处于逐步推广过程中。机械化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面貌,小农经济日益卷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小农生产的村社自主性逐步瓦解。
小农与机械化的结合打破了人们对小农经济的习惯性偏见: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户家庭,因为土地细碎,不具有购置大型农业机械的动力,因而难以实现机械化。由此引出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构和改造农业经营主体,但这种思路忽视了小农户与社会化体系对接的现实可能性。社会性小农的能动性构造了 “社会化小生产”(杨建华,2008)的小农经济现代图景。
在同等生产条件下,农户若自购机械为自己服务,因为涉及到田块的变换,且面临着“过田”的可能,确实存在农田细碎导致的效率损失。但若依托机械化服务体系,则农户因自购机械和自我服务而产生的困难就不存在了。调研也发现,农户即使购买农业机械,除自用外,也主要用于在本村即周边提供有偿服务,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少有农户的农田面积能够达到机器的负载面积(即机器的充分有效利用),而即使达到了较大规模的承包面积,但农地分散的负面效应也会随着面积增加而进一步强化,遏制了承包大户购买农机自用的激励强度。
按照市场的逻辑,机械服务提供者追求的是利润,利润只有通过规模效益才可以实现。因此,机械化只能以“面”的形式对接小农。面对一家一户农户零碎分割的现实,农户唯有联合一致,才能凑出成片的土地吸引机器前来,也唯有在农作时间上的高度协调,才能使尽可能多的农户纳入到机械化服务之中:“在路边的,你搞早一点,还可以,但里面的,晚点都好些。种的时候和收割的时间,事先我都会问好,包括品种、育秧时间,以及成熟期。不然就要等来等去,遇到变天,还对产量有影响。”“现在,一切都要快。以前都慢。现在,慢了就不行了。人家搞完了,你走都走不成了。……你一块田落在后面了,人家都收割完了,收割机不会为了你一家专门跑过来。”
当然,如果靠内的田作物较早成熟而不愿等待,也可以请收割机从外面的田割出一条路,事后农户之间再协调补偿事宜,这就产生了较高的协商成本和一定的经济损失。此外,一些小块田地较多的农户,只有依傍邻近农户的大田,才能在收割的时候“搭售”出去:“小田就只能和别人的大田一起请。我以前,最大的一块才8分,请收割机的时候,我说:这块大田是我们的,但你先把我旁边的小田收割了……怕割了大田,不给我割小田了。”
面对社会化服务体系,社会性小农主要通过外向协作与之对接,内向互助随着农村生产要素的变化而逐渐丧失自主性,并服务于外向协作的需要。比较典型的是当前农村日益普遍的“联户”耕种模式。例如,金村一个村民小组,目前在村种田的只有8户人,共150亩田。农民之间通过合伙的方式,一共购置有4台小型插秧机和5台12匹拖拉机。这个湾子的150亩的土地均通过联户的方式进行,即2户或者3户一起搞。该村民组的组长讲到:“年轻人不在家,老人一起来搞。外面的收割机过来了,都是一片一片地收过去。一户收割,其他相邻农户则开着拖拉机前去帮忙。5亩田烧一餐伙。欢乐得很,不觉得吃亏,又好玩。”
上述案例比较典型地呈现了社会化服务体系下社会性小农的微妙变化。田块相近的农户出于机械化收割需要形成紧密协作,并且通过收割这一环节而传递到农作过程的其他环节。同时,机械化也改变和重构了内向互助的形态。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小农生产关系还体现了一定的村社自主性,那么,第二阶段的小农生产关系则体现了社会化体系的主导性,社会性小农服务于对接社会化生产体系的需要。“田友”因而成为农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过田,要先打招呼!关系不好的,走空田,也要和别人说!关系好的,走空田,就不用说。去年,一户人家不让别人走,闹纠纷,指甲都打断了。”在农民的日常人情交往中,“田友”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关系类型。
总而言之,社会性小农实际上构成了“社会化小农”的微观基础。如果离开了小农生产之间的社会性协作,小农生产的社会化状态将失去存在的有效基础。
五、小农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税费改革进一步弱化了集体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小农经济进一步陷入“单干”状态。在唱衰小农经济的话语中,这种“单干”状态无疑是低效的。但调研发现,江汉平原的小农经济并未随着集体退出而陷入解体和停滞,反而通过适时地顺应社会化服务体系而持续发展,并达到了较高的机械化水平。
从小农生产的制度体系来看,村社生产体系的弱化并没有导致小农经济的停滞不前。村集体从农业生产服务中退出固然也为农业生产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农田水利困境导致农民灌溉难度和成本增加。但如果着眼于宏观层面小农经济本身的演化,就会发现,即便是面临村社体系弱化带来的一系列困扰和问题,小农经济的体系也日益融入开放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自身的调试,逐渐走向“社会化小生产”。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较好地解决了小农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对接的难题(王建华,李俏,2012),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小农经济逐渐迈向现代化。小农经济内部逐渐发生的这种适应性变迁过程,笔者称之为小农经济的发展。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表现为农业的资本化过程。根据视角不同,“资本化”有两种定义: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角度对资本化进行定义,即“资本对劳动比率的上升”(萨缪尔森保罗,诺德豪斯威廉,1991);政治经济学则从生产关系角度进行定义,“资本化”表现为小农与土地分离和农业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转型(亨利·伯恩斯坦,2011)。目前,政府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尝试,实际上侧重于再造农业生产关系。黄宗智(2012)主要从生产力的角度定义资本化,并且发现,在过去20年,中国农业发生了实质性的资本化(即单位土地资本投入不断增加,而农业雇佣关系并未普遍形成),并将此过程称之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并不具有必然性。沙洋县的小农经济发展经验也说明了这个过程:以机械化为核心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小农家庭结合,超越了村社体系之下的小农经济格局。
小农之间的相互合作,使得分散的小农生产与社会化分工体系提供的专业化服务(尤其是机械化服务)对接,现代生产技术和资本要素因而可以进入小农生产过程。小农经济的发展因而呈现为不同于主流学界设定的演化路径。他们对农业经营主体的聚焦忽视了主体之间的生产关系及其能动性适应。基于小农生产结构的规定,这些微观层次的生产关系表现出相对独立性和自发性。伴随着农业生产体系的社会化,机械化的进入逐渐压缩了农作参差期。传统农业技术下春耕要忙碌一个月之久,现在的机械化则将春耕插秧农忙时间缩短到10天左右。“农忙”的时间分布日益集中,农民的农作安排主要不再参考自然节气及其自然参差期,而是参照其他农户的农作进度。
反过来看,在土地细碎化的情况下,如果小农各自为战,这将导致机械化难以推进,中年农民种田的机会成本增加,老人种田也将因劳力不足而存在规模限制和年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向资本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就会较高,土地的大规模流转便具有了群众基础,小农经济的演化更有可能突破其原有框架,导致小农经济的资本主义转型。
社会性小农是小农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社会性小农的弹性使得小农家庭之间通过不同的合作模式可以适应不同的农业生产体系:社会性小农通过生产过程中的自发秩序,降低了村社体系的服务供给与农户家庭生产之间的协调成本。伴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育和小农的社会化,社会性小农成为与社会化体系对接的基础。社会性小农通过强化外向协作,使得不规则的小农生产被纳入到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之中,缓和了小农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之间的张力,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
市场化体系的发达并不意味着小农的“原子化”,社会性小农的弹性赋予其有效接应和对接社会化体系的能力。小农家庭之间形成的生产合作并不是一般所讨论的“合作社”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形态,而是基于传统村社熟人社会的非正式的自发性关系结构。合作社的“名实分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熊万胜,2009)。与之相比,社会性小农富有弹性的非正式结构能够随着小农的社会化而调试和转化,它既延续了小农经济的村社互助传统,同时也适应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最后,它也使得小农能够有效应对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小农经济因而呈现为适应性变迁的发展路径。
五、结语
有学者立足于农民家计模式,从“半工半耕”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式小农经济的韧性(贺雪峰,2013)。社会性小农这一概念则从社会学视角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对小农经济的理解。不理解社会性小农及其运行机制,便难以理解“半工半耕”机制的社会基础,社会性小农因而是中国式小农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深层基础。
小农生产关系中社会性合作构成生产关系的基础结构,而浮动于其上的则是变迁中的生产体系。依托这个富有弹性的生产关系基础结构,分散的小农深度参与和适应了外部社会化生产体系,以农业机械化为典型标志的小农经济发展得以可能。小农经济的发展逻辑揭示了小农经济的内在活力和适应能力,由此可见,规模经营主体并非小农经济与机械化结合的必然基础和唯一路径。其政策启示在于,政府的农业治理不应采取消灭小农经济的激进思路。当前政府采取的诸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进一步破坏了小农经济的自发成长过程(孙新华,2013)。
政府的农业治理需要正视小农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事实上,社会性小农的弹性具有内在的限度,伴随着社会性小农弹性空间的逐步缩小,农户合作成本也有所增加。社会性小农的限度预示了农地制度创新的空间。沙洋县目前以农地确权为契机,推行流转并地试验,缓解土地细碎化带来的不便,通过赋予农户生产自主性,进一步释放了小农经济发展的活力(孙邦群,刘强,胡顺平,罗鹏,2016)。如何从社会性小农向个体性小农转变,进而更为充分的理解小农经济的发展路径,这是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的问题。
致谢:王海娟和夏柱智对本文提出了细致且富有启发性的修改意见,特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1.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华夏出版社, 1991
2. 曹东勃. 小农经济改造与中国农村改革. 财经问题研究,2009(01):116-122
3. 费孝通,张之毅. 云南三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5
4. 冯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农业治理转型——基于皖南平镇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2015(02):23-32
5. 贺雪峰,郭亮. 农田水利的利益主体及其成本收益分析——以湖北省沙洋县农田水利调查为基础. 管理世界,2010(07):86-97
6. 贺雪峰. 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1-6
7. 亨利·伯恩斯坦. 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 侯方安. 农业机械化推进机制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启示——兼论耕地细碎化经营方式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 中国农村观察,2008(05):42-48
9.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 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 开放时代,2012(03):10-30
10. 刘显利.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选择逻辑及其演进——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研究对象. 求索,2013(08):74-76
11. 马克思. 资本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 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组织.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13. 宋丽娜. 熟人社会的性质.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118-124
14. 孙邦群,刘强,胡顺平等. 充分释放确权政策红利——湖北沙洋在确权登记工作中推行“按户连片”耕种调研. 农村经营管理,2016(01):27-30
15. 孙新华. 农业经营主体:类型比较与路径选择——以全员生产效率为中心.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2):59-66
16. 王建华,李俏. 农业社会化服务视域下的农民互助研究. 农村经济,2012(12):117-120
17. 熊万胜. 合作社:作为制度化进程的意外后果. 社会学研究,2009(05):83-109
18. 徐勇,邓大才. 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 学术月刊,2006(07):5-13
19. 杨建华. 社会化小生产:一个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现代化实践的研究. 上海经济研究,2008(7):3-19
Social Small Farmers: The Soci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based o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han Plain
Du Peng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farming jagged period, the division of fragmented farms and the agriculture link relevance, small farmers present a strong social production relations. Social small farmers is the real subject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operation, which use different ways to allocate resources reasonably and arrange production effectively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of the small-scale peasant household produc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elasticity of the social small farmers means that it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governance cost of the rural production system, but also can docking the socialized production service system effectively, which creates the condi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capital, technology and land. Small-scale farmers lead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of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Key Words: Social small farmers; Th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Development;Adaptive change
本文原载于《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