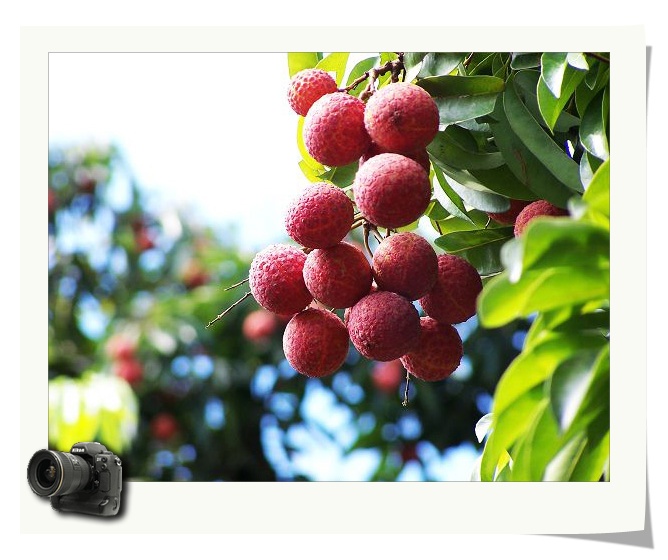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及其拓展
孙新华
(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我国快速的农业转型现实迫切要求农业转型研究的跟进,而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研究无疑在其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梳理既有研究有利于找准当前研究的位置和进一步拓展的路径。研究发现,“社会中心范式”和“国家中心范式”下的研究虽然为我们搭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但却存在着“只有社会没有国家”或“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只有国家没有地方”的不足。结合我国的农业转型实践,可从丰富国家视角、构建综合解释框架和关联相关研究等路径进一步拓展研究。
关键词:农业转型;动力;社会中心;国家中心;地方政府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快速而又全面的转型之中,农业也无法置身其外。甚至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农业中姗姗来迟的资本化转型将农业转型这一问题已经变成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核心问题[1]。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下分户经营的耕地制度,所以,农业转型是伴随着土地流转而展开的。
近年来,我国农村的土地流转正在加速进行,从而带动了我国的农业转型。据统计,2006年我国耕地流转面积只占到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4.57%,之后土地流转的速度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2008年为8.6%,2011年上升到17.8% ,2013年6月底上升到23.9%,2014年6月底增加到28.8%,截至2015年底达到33.3%,是2006年底的7.3倍,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4.47亿亩。短短十年,土地流转发生如此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伴随快速的土地流转而来是“突破性农业转型”,其中体现在农业经营主体的转换、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2]。因此,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影响必定是深远和全面的。
面对这种迅速而又剧烈的转型,我们不禁要问我国的农业转型将走向何方?现实的农业转型将对我国农民、农村和农业产生何种影响?农业转型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而在笔者看来最后一个问题尤为关键和重要,因为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直接决定了现有的农业转型形态,进而影响着农业转型的具体方向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因此,探究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在农业转型研究中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
本文试图在梳理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研究主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在我国现实国情下深化和拓展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研究的具体建议,以增进对当前我国农业转型的解释和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
农业转型作为一个经典学术命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产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业转型的方向上,即家庭农业到底是能够顽强的生存下去,还是终将为资本主义农业所替代?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坚持认为家庭农业必将被资本主义农业替代,主要以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代表;另一派则坚信家庭农业具有明显的合理性,未来仍将是农业结构的主体,主要以恰亚诺夫派和舒尔茨为代表[①]。尽管以上两派关于农业转型方向的判断截然相反,但是他们在论证农业转型动力机制上却坚持着共同的范式——“社会中心范式”,即它们都认为农业转型无论转向何方,都是由经济社会因素自发决定的,而不是由国家推动的。为方便起见,笔者下面主要选取两派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分析。
1.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农业转型动力
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随着商品化的发展,家庭农业将让位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而这一过程是在被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推动下实现的。在自由主义经济学里,亚当·斯密至今仍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代表作《国富论》中,农业转型显然不是斯密讨论的重点,但他也明确指出“资本进入农业,将会导致更多农场‘佣人’的劳动投入”[3],其言下之意是说,在农业领域雇佣型农场将是农业转型的方向,正如在工业领域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工厂化大生产必将代替小作坊一样。其论证的主要逻辑是,在“看不见的手”的调整下,技术革新将推动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这将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实现规模经济,从而使规模生产战胜了小生产。在斯密的理论里,市场最为核心,他认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个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就会自发地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斯密主张以劳动分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没有政府干预的国家财富增长理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的强调和对政府的贬抑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国家对市场来说不过是一个‘低级工人’而已;市场似乎有着一种独特的力量,无须外界的太多辅助就可以保证经济体的协调运行”[4]。政府只需维护好基本的社会秩序、保护好公民的财产权,市场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增进个人利益和社会福利。在这样的认识里,市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自然也是农业转型的主要推动力,而国家是没有发挥作用的,即使有什么作用也几乎可以忽略。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事实和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基于大规模雇佣劳动的农业),并且应该如此”[5]。
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认为资本主义农业必将替代小农农业,而且认为这一农业转型的动力来自商品经济下的技术革新。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论证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时更加细致和明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到,“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运用所替代”[6]。恩格斯的观点也相差无几:“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越来越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7]。马克思说到的“大工业”和恩格斯所说的“机器和蒸汽”都属于技术革新的方面。当然,这种技术革新不仅包括机器的使用,还包括“土壤的改良、化肥的使用、更优物种的农场牧畜的饲料和使用、在企业内部对原产品的进一步加工、一种更成熟的劳动分工、对劳动的有计划组织,等等”[8]。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农业相对于家庭农业的优越性。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以上逻辑,他认为,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形式,小农必然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其施加的压力下逐渐消亡。小农消亡的过程是社会分化的过程,列宁预见小农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分化成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两个社会阶级。小农分化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各个小农采用农业改良技术的方式、速度不同,小农因为无法与更先进的农民在市场上竞争而被迫失去财产与生产资料,而那些成功农民却越来越多地雇佣农业工人[9]。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业转型的解释也主要是从经济因素尤其是技术变革和商品化着手的,国家的作用也是被忽略的。这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而已,不需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单独分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0]。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国家是不具有“自主性”的,因此,没有将国家纳入其对农业转型的解释框架。
在学术界,倡导家庭农业的学者应该以恰亚诺夫和舒尔茨最为著名。虽然他们在研究进路上存在很大差异[②],但是他们都主张家庭农业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形成了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截然相反的一派。因此,笔者姑且将他们统称为“家庭农业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纠正了主流认识对小农生产的偏见——不仅低效而且非理性,认为小农生产非常高效和理性。因此,他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正确途径,不是发展苏联式的大农场,而是保留家庭农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向农民提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民一旦认识现代生产能要素的优越性,便会毫不犹豫的接受,从而推动农业的现代转型[11]。因此,舒尔茨眼中的农业转型是在保留家庭农业的形式基础上为其农业注入现代生产要素,使其由传统农业转型为现代农业,从而实现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舒尔茨在农业转型方向的判断上与斯密相反,但是他们在转型动力上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黄宗智曾经归纳道,“舒尔茨保留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的质变推动力的最初设想的核心,同时又考虑到小农农业生产的持续”,他们“同样把市场刺激当作乡村质变性发展的主要动力”[12]。在舒尔茨的解释框架里仍然是没有国家的位置。这是因为舒尔茨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员同样秉持其基本的信条,即政府与市场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必须在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制度环境下才可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合理配置资源”[13]。
作为列宁的辩论对手,恰亚诺夫认为小农不会像列宁描述的那样日益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只是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内劳动者与消费者比例的变化而起伏,但始终不会突破家庭经济的范围。因此,他断言小农家庭农场具有“强大抵抗力”和“历史稳定性”[14] ,农业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基于合作组织形式的纵向一体化,而不是苏联式的横向一体化[14]。简言之,恰亚诺夫理论中的农业转型主要是指小农家庭农场内部的分化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组织的纵向一体化。其中,小农农场的分化主要是自发形成的,这一点恰亚诺夫表达的非常明确。他指出,俄国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由“1850万个分散的小农民农场形成的自发力量,其发展受制于各种自发的因素,基本上不受国家控制” [14]。这些自发的因素既包括随家庭生命周期发生的人口分化,又包括市场状况在内的各种“纯经济原因”,当然,前者起到“主导性的作用”[14]。但是在强调合作制的纵向一体化时,恰亚诺夫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他说,“如果我们不希望动摇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稳定性与弹性机制,那么就不能听任国民经济一个最主要部门的发展处于某种自发的状态……我们还必须致力于对自发的农民农场进行直接的组织控制……以此把每一个农民农场汇入计划经济的主流” [14]。因此,在恰亚诺夫的理论里,农业转型的动力既有自发因素又有国家干预,即使在发展纵向一体化时启动国家干预,但基础力量仍然是自发因素。因此,黄宗智等人认为恰亚诺夫提出的纵向一体化是“一条通过市场化的农民合作组织来实现的发展道路”[15]。
4.国家的缺席及其不足
以上简单爬梳了有关农业转型的主要理论对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它们在解释农业转型动力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层面的市场机制、技术更新或者是社会层面的人口分化,其中市场机制是他们共同认同的农业转型推动力。而国家力量在这些解释框架内都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因此,都可将这些解释归入在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占据主流的“社会中心范式”。在这一范式下,社会变迁主要被解释为经济社会自发力量推动的结果,国家或者被视为各种力量相互竞争的平台或者被看做统治阶级的工具[15]。因此,国家是不具有主体性的,也无法构成社会变革的推动力。正如斯考克波指出,“现代社会科学随18世纪和19世纪西欧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一同出现,因而很可以理解其奠基性理论家会认为社会的变革动力以及社会利益不是来自过时的、早已被取代的君主制和贵族制国家,而是来自公民社会——不同的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如理解为‘市场’、‘产业劳动分工’或者‘阶级关系’等等” [15]。
不可否认,以上学者基于“社会中心范式”所做出的研究对解释农业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各种理论指出了在自发状态下小农农场和资本主义农场所具有的优势及其影响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对于小农农场长期存在的影响许多都是相互对立的,既有分化力量又有稳定力量,而这些对立力量的相对强弱却受到外界力量的影响,其中国家就是一个非常常态而有力的外力[16]。当将国家纳入到农业转型动力中,转型模式就不会像主流理论描绘的那样单向和线性,它会根据国家干预的不同程度而有所不同。
而从现实来看,由于农业在任何社会都处于基础性地位,具有自主性的国家力量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干预农业的发展。因此,现实中国家在农业发展和转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直接影响了农业转型的方向和效果。即使在被奉为自由主义圭臬的美国也不例外,美国事实上长期干预和扶持农业,仅美国联邦政府当今每年补贴全国农场的资金就达200亿美元[13]。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转型中,国家干预更是非常普遍和深入,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据此有学者将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国家称之为“发展型国家”[17]。反观我国,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农业变迁都与国家的干预密切相关。这些鲜活的事实都说明“社会中心范式”忽视国家作用存在严重不足,需要在解释农业转型时引入国家的视角。
针对“社会中心范式”中只有社会而没有国家的缺陷,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找回国家”的学术思潮,力图将国家作为重要变量来解释社会变迁,从而形成了不同于“社会中心范式”的“国家中心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将国家纳入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变化的解释变量中,并将其重新置于中心地位。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将国家力量作为农业转型的内生变量加以研究,并从国家的视角探究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贝茨、斯科特和哈特等人。
1.贝茨的国家干预分析及其不足
罗伯特·贝茨是当今美国最具影响的发展政治经济学专家,同时也是国家主义学者中的一员。他在研究农业问题时主要意图就是,纠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忽视制度和政治的倾向,揭示政治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在其代表作《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18]中,贝茨看到,在热带非洲国家的农业政策主要通过干预市场来影响农业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通过价格政策控制涉农市场的价格来制造工农业部门之间的“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资本积累,为城市居民提供廉价农产品;另一方面,为了增加国内粮食产量,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剩余中拿出一部分返还于农村,对种子、化肥、机械、贷款等进行补贴。然而在这两个资源流动方向完全相反的过程中,受益的却都是少数利益集团:在提取资源的过程中主要是企业家、官僚、城市工人和市民得利,而在反哺农业的过程中获利的主要是农村的大农场主,而广大普通小农场主在这两个过程中都是受损的。同时,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的补贴政策还导致大农场主在农村得到迅速扩大和发展,甚至在有些原本没有地主的地区再造了大量地主出来,而小农场则被冷落和边缘进而被替代。
对于这些现象,贝茨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给予解释。关于剪刀差的出现,贝茨认为,一方面是国家有意识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面对强势利益集团(包括企业家、官僚、工人和市民)的施压,政府为了保持政治稳定而不得不做出对农民的牺牲。而之所以对农业生产的补贴主要落入了少数大农场主的手中,大多数小农场主却得不到这些项目补贴,绝不是实施过程中的意外后果,而是政府出于政治考量而有意为之的结果。他认为政府在促进农业发展时,不是选择普惠性的提高粮价政策而是政府操作空间更大的项目政策,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政治控制。因为价格政策会使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获得利益,而项目的政策则可以使政府有针对性地分配资源:“通过允诺利益,他们可以寻得合作;通过赠与,他们可以获得顺从;而通过收回利益,他们可以惩罚那些反对者”[18]。正是利用补贴项目,政府在农村建立了有组织的政治支持。政府之所以选择大农场主作为补贴对象,是因为他们在农村是极具影响力的势力,而且他们比分散的小农更容易集结起来影响政府决策。
在贝茨的研究中,市场是受政治控制的,政府通过干预市场来提取资源并进行再分配,从而推动了农业转型。而这些都是为了当权政府实现更好的政治控制。在此,市场成为了政府政治控制的工具。这既批判了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的迷信,又凸显了国家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贝茨的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与其他国家主义学者一样,贝茨在分析中过度地凸显了国家的作用,而对社会一方的主动性揭示的不够,似乎社会一方只会默默承受国家带来的影响而无所作为,而这显然不符合现实情况,此其一;其二,在贝茨的论述中国家是铁板一块的,内部的层级之间是没有张力的。而实际上,在国家内部各个层级的政府及其官员都具有自主性,因此需要进行区别对待。应该说,以上两点不足都限制了贝茨研究的全面性和丰富性。
2.斯科特的国家视角及其缺陷
相对于贝茨主要探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斯科特关于农业转型的研究则主要是在国家与社会框架下展开的。在《国家的视角》[19]中,他利用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以苏联的集体化和坦桑尼亚的村庄化为例探讨了工业化农业的运作逻辑。两个国家虽然在一些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它们所做的都是利用国家权力使农业由分散的小农经营转向集中的集体农场经营。这样的大型社会工程之所以会发生,在斯科特看来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两国领导人都抱有极端现代主义信念,这体现在农业发展上就是对“大型、机械化和工业化农场的迷信”[19]。第二,国家管理和控制的需要,无论是国家征收赋税还是政治控制,都要求国家对社会进行清晰化和简单化的设计,而相比分散的小农,集体农庄显然更符合这一要求。第三,独裁主义的国家,这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得以实现的权力基础。第四,软弱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国家项目的能力,构成这些项目得以推行的社会基础。斯科特认定,正是以上四个方面的“致命结合”才导致了这些社会工程得以发生。
斯科特认为,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苏联和坦桑尼亚的农业改造无疑是成功的。通过改造农业,国家在农村建立了便于自上而下进行监督、管理、征税和控制的新的制度形式和生产单位。但是,他认为从更多的方面来看,这一改造又是失败的:粮食产量下降、生产效率低下、生态退化、给农民生活带来巨大灾难,因此并没有实现其设计者的初衷。至于这些项目失败的原因,斯科特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内在矛盾进行解释的。在他的认识里,国家机器的核心在于简单化和清晰化,而社会一方(包括农业生产)则由于地方知识、实践和背景等特殊性的存在而无比复杂。国家在实施项目中往往将社会的复杂性、不清晰、地方性知识和实践视为落后并将其移除,从而导致了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终告失败。因此,斯科特建议,国家对于社会的复杂性应该少一些傲慢多一些尊重。
斯科特的研究对于改造农业运动的发生和失败都给予了独特的解释。在其解释中,国家机器处于中心地位,国家征税和控制的需要本能地要求农业生产单位和制度的简单化与清晰化,这与社会本身的复杂性构成尖锐的矛盾,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构成了其最终失败的原因。正如诸多论者已经明确指出的,尽管斯科特的分析很吸引人,但是却始终固守“农民—国家”、“传统—现代”和“抵抗-支配”这种僵化而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19-20],在这种模式中国家与社会总是对立和矛盾的,而且似乎国家的作为总是带来麻烦,而社会的做法都是十全十美的[③]。其实,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存在对立也存在着合作与共谋,而且国家的所作所为不仅有恶的一方面也有好的一方面。同时,斯科特在承认地方社会复杂性的同时却将国家简单化了,忽视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在这一点上,斯科特和贝茨是一致的。
3.哈特等人的权力运作逻辑及其问题
除了以上两位学者,哈特等人的研究也非常值得一提。哈特等人在他们的论文集《农业转型:东南亚的地方进程与国家》[21]中集中探讨了国家在农业转型中的权力运作及其作用。他们在研究东南亚四国(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绿色革命期间的农业转型中发现,既有研究主要从纯粹的技术进步和商品化角度来分析农民分化和农业转型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将国家的权力结构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因为从来就没有一种普遍的农政分析范式可以概括不同语境下的农业转型过程,农业转型过程是嵌入在复杂的、多过程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的。这样,经典著作所建构的“商品化、技术进步→农业结构变迁→农民分化”模式,就会因为加入了国家干预及其权力结构这个中介变量而具有了多种变迁的路径和具体形态。因此,他们主张要将地方层次上的农业转型的经验过程和宏观层次上的政治-经济系统关联起来,关联这二者的核心要素正是不同层次上的权力结构,进而国家权力和地方精英在推动农业转型与农民分化过程中发挥着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
他们的解释路径被归纳为代理人逻辑,其内在机制为:这些东南亚国家在绿色革命期间,国家为了追求在农业部门内外、复杂的、经常是存在相互矛盾的利益(比如技术进步、粮食产量增加、维持粮食低价格、保护城市消费者的利益)等等,需要在农村寻找实现国家意志的代理人,一方面通过这些代理人实现国家的农业改造计划,另一方面也同时需要控制乡村社会秩序。进而,农村地方精英比如大地主、农场主成为国家实施农业改造计划的代理人,国家对这些地方精英进行农业补贴来调动这些代理人的积极性,进而农村地方层次上的地方精英成为绿色革命过程中的直接受益者而与国家一拍即合。国家对农村精英阶层的这样一种补贴,改变了农业的阶层结构和生产关系,推动了农民的无产化,以及农村的贫富分化。可以说,国家对这些农村强势群体的补贴是推动这些国家农业转型的决定性力量,这不仅影响了这些强势群体的汲取与积累的形式,而且所产生的紧张和矛盾构成农业转型和农村社会分化的源泉[22]。
哈特等人的研究虽然与贝茨的研究在对话对象上不同,但是他们所运用的解释路径和研究结论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他们在研究上所存在的问题也具有相似性。
当然,以上三组学者的研究并不能完全代表运用“国家中心范式”分析农业转型的所有研究。但是他们在弥补“社会中心范式”的不足和其运用“国家中心范式”中的缺陷却具有极强的代表性。总之,他们都致力于将国家变量引入到对农业转型的解释,这相对于主流基于“社会中心范式”所做出的研究是一个革命性的跨越,对于我们研究我国的农业转型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与此同时,这些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显。由于他们要区别于“社会中心范式”的研究,而更加注重分析国家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之对社会这一重要环节的分析往往不够深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将国家内部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在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同时也忽略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不仅仅只是按部就班地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他们本身也具有“自主性”或“主动性”[23]。以上两个方面的缺陷限制了“国家中心范式”的研究,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研究留下了空间。
通过对既有研究的简单爬梳,可以发现,“社会中心范式”和“国家中心范式”各有侧重,分别从经济社会视角和国家视角研究了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为我们理解农业转型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但是两种研究范式本身也都存在显见的不足。如何克服“只有社会没有国家”、“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和“只有国家没有地方”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构成了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研究进一步拓展的方向。正如本文开篇所言,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快速转型时期。这既为研究者提出了对其加以解释的现实要求,也为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化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研究的经验素材。因此,结合我国的农业转型实践来拓展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研究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切入。
1.通过揭示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型的机制与逻辑来丰富国家视角
正如前文所言,“国家中心范式”在对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的研究中过度强调国家相对于经济社会因素的自主性,而忽略了国家内部的差异和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从而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我国现实中的农业转型实践来看,地方政府都具有相对于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自主性,不仅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很多时候甚至不惜违背中央政府的政策来推动农业转型。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深入揭示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型的具体机制和逻辑,即地方政府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推动当地的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发展,这些措施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地方政府实施这些措施背后又遵循着何种逻辑?唯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我国农业转型的直接动因,因为各地的农业转型中来自国家方面的推动力量首先是作为直接管理者的地方政府。进而,通过强调农业转型的地方推动力,也能丰富“国家中心范式”对农业转型的研究。这种丰富既体现在从国家自主性之中分离出地方自主性并探究其对于农业转型的影响,又体现在对国家自主性与地方自主性相互作用的探讨。这不仅要求要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农业转型中的推动作用进行分析,还要注意两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及其对农业转型的影响。
2.通过融合“社会中心范式”和“国家中心范式”来建构综合解释框架
通过梳理两种研究范式对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的研究,可以发现,两者基本都是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下展开研究的。因此,造成了“只有社会没有国家”或者“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局面,从而使其对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的研究陷入片面,也抹杀了现实经验中经济社会因素与国家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鉴于此,亟需在融合“社会中心范式”和“国家中心范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农业转型实践,将作为推动力量的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国家因素(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纳入研究视野,分析各种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建构出一个更富解释力的综合分析框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作为农业转型基本推动力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农业转型的作用方向和作用机制是什么样的,两种因素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当国家因素介入进来后以上图景又会发生何种变化,国家干预程度的不同又会带来什么不同的影响?经济社会因素又是如何反过来影响和制衡国家因素的?这些因素通过综合作用又会对农业转型产生何种影响?只有研究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在此基础上搭建综合的理论模型。
3.基于以上研究深化农业转型动力与农业转型方向等方面关系的研究
笔者在开篇已经指出,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研究在农业转型研究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直接影响了对农业转型方向的判断和对农业转型影响的认识等。而现有对农业转型方向和农业转型影响的研究基本都是在“社会中心范式”或“国家中心范式”下做出的,从而使其解释力大打折扣。比如在“社会中心范式”下形成的针锋相对的两派,都坚持认定农业转型方向具有单向性和普适性,即不是资本农业代替家庭农业就是家庭农业战胜资本农业。而当将国家因素引入进来,他们对农业转型方向的判断就会因为不同的国家干预程度而发生不同的变化。反之,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农业转型方向的影响也不是单向的,更不是普适的,而会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所以,当我们将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的综合视角纳入进来,既有有关农业转型方向等问题的研究也需要做出调整。而具体要做出何种调整,就需要在现实的经验中将农业转型动力与农业转型方向等问题勾连起来,将其纳入综合的解释框架的链条之中。
综上,我国资本化农业转型虽然姗姗来迟但是却异常迅猛,如何对其加以解释并对其发展方向做出判断,又如何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积累相对深厚的农业转型研究进行推进,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不揣浅陋,在粗略梳理有关农业转型动力机制主要研究范式及其解释逻辑的基础上,对在我国农业转型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求教于各位方家,以共同推进农业转型研究。
参考文献:
[1]张谦.中国农业转型中地方模式的比较研究[M].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10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3-27.
[2]孙新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兴起与突破性农业转型[J].开放时代,2015(5):106-124.
[3]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Smith, 1976.
[4]普雷斯顿.发展理论导论[M].李小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J].开放时代,2012(3):10-30.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补充译者.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恩格斯.论权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考茨基.小规模农业的竞争力[M].何增科,周凡.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9]列宁.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2]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3]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4]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6.
[15]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M].方力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6]弗兰克·艾利思.农民经济学[M].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7]禹贞恩.发展型国家[M].曹海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18]罗伯特·贝茨.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M].曹海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19]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0] 朱晓阳.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1]Gillian Patricia Hart, Andrew Turton, Benjamin White. Agrarian Transformations: Local Processes and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2]龚为纲,张谦.国家干预与农业转型[J].开放时代2016(5):57-75.
[23]托马斯·海贝勒,舒耕德,杨雪冬.“主动的”地方政治:作为战略群体的县乡干部[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3.
Study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Agrarian Transition and Its Expansion
Sun Xinhua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Abstract: The rapid agrarian transition in China urgently requires the follow up of agrarian transition research in which the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agrarian transition is undoubtedly the basic position. Comb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helpful to identify the position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further expand the research path. The study find that the research under sociocentrism paradigm and nationalism paradigm has set up a bas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s, but there are the deficiencies of "only the society without the state" or "only the state without the society", "only the state without the local". 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e of agrarian transition in China, we can further expand the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agrarian transition from enriching "seeing like a state",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and associating the related research.
Key words:Agrarian Transition; Force; Sociocentrism; Nationalism; Local Government
[①]当然,在以上两派内部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此处将它们归为针锋相对的两派,只是根据它们对农业转型方向的判断大体相似,不代表它们内部在学术立场和论证方法上都具有一致性。
[②]黄宗智将恰亚诺夫称为“实体经济学”的首要代表,而舒尔茨则为“形式经济学”的首席代表,针锋相对。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页。
[③]这与斯科特本人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密切相关,朱晓阳曾指出斯科特曾明确表示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参见朱晓阳:《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页脚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