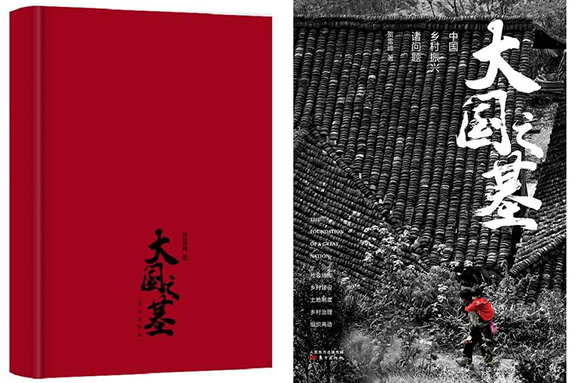社长说
此前,社长推送过耿羽丨拆迁“宫心计”,探讨了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复杂博弈,犹如“宫斗剧”和“谍战片”。那么,征地拆迁的博弈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呢?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土地制度与“城市化”、“市民权”的内在关联?刚好,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贺雪峰教授的专著《大国之基》出版了,而土地制度正是该书重点讨论的内容之一。于是,社长邀请到林辉煌博士,为我们讲讲《大国之基》中的土地问题。欢迎社员们踊跃投稿或留言参与讨论!
1《大国之基》与土地制度
贺雪峰教授的新书《大国之基》终于出版了。这本书延续了作者近年来有关三农问题的探讨,进一步用经验和逻辑打破经常被掩藏在道德情绪之下的村治逻辑。如作者说言,“没有分析就没有政策,尤其是当前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发展十分不平衡,如果没有对发展战略的深入分析,我们就可能在制定政策中犯低水平的错误”(第3页);而要获得对三农问题的深入分析,只有依靠饱满的经验调查和不带情绪的机制分析。通篇看来,作者确实很好地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从而使这本新著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教义性。全书除了导论之外,由“社会结构篇”“乡村建设篇”“土地制度篇”“乡村治理篇”“组织再造篇”共五部分构成,几乎完整含括了农村问题的所有核心领域。这五部分都有很多新的发现,受篇幅限制,本文将重点谈谈“土地制度篇”给笔者带来的启发。与《地权的逻辑》系列著作相比,本书对于土地制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包括宅基地、增减挂钩、征地冲突、地权意识等。这些篇章具有浓厚的论辩色彩和经验机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土地制度的常识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被发现的!在我看来,《大国之基》对于土地制度的论述,其基本目标在于还原两个土地制度常识:一是不给政府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制度不利于城市化的良性发展,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二是不顾及非城郊农民利益的土地制度将造成社会的动荡甚至分裂。这两种常识判断,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最广大农民的利益。有趣的是,同样是“维护农民的利益”,主流的学者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这些判断可以统辖于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市民权”理论下,或者称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城市化”理论。“市民权”理论主张,中国的城市化应当是农民的城市化,是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收入并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城市化。围绕着“市民权”的理论,主流学界对土地制度的安排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主张。第一种主张集中关注正在遭遇征地拆迁或者即将遭遇征地拆迁的农民,认为所有土地增值收益都应当由这部分农民独享;而当前的土地制度实践显然没能使这些农民获得完全市场化的收益,从而阻碍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第二种主张认为即使是非城郊农民也应当享受城市化的好处,但是他们必须拿自己的宅基地和耕地来置换“市民权”的待遇。第三种主张也关注非城郊农民的“市民权”,认为土地增值应当为全民共享,并且无需非城郊农民以自己的土地来交换,当然,政府不应当在其中有所染指。
2“市民权”的三种方案
上述三种“市民权”理论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判断却是相同的:政府不应当分享土地增值的利益,否则将影响“市民化”的进程。这一判断是错误的,而且对于国家发展来说也是极为有害的。政府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可以有两种理解:1、政府利用一部分的土地增值收益,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城市化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也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2、政府将一部分的土地增值收益化公为私,据为己有。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情况显然都存在,但是学者们往往以政府可能腐败为由来反对土地财政,而完全忽略了丧失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化的消极影响。对于后发展的地区,如果没有土地财政,城市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很难完成,而没有基础设施的城市化显然不值得我们期待。实际上,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或者落在政府或者落在市场的头上。显然,搞基础设施是不容易赚钱的,市场主体往往不会积极介入,除非它能够从土地增值收益中获得更大的好处。政府是不允许赚钱的,因此一般认为搞基础设施就是它的责任,如果它不能将土地增值收益中的一部分转化为基础设施的成本,那么就只能挪用纳税人的钱,而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满足其他更多的公共需求。事实上,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经常都捉襟见肘,根本不够用来搞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政府分享一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用以搞基础设施建设有何不可呢?当然,政府也可能贪污,但是对这些越轨行为,可以约束它、制裁它,但是没有理由因此而将政府能力削弱,否则我们就犯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因噎废食困境”。因此,不允许政府分享一部分的土地增值收益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要么陷于拉美式的贫民窟,要么被迫采取极高成本的城市化方案(政府买单的“市场化”?),而这两者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显然是极为不利的。虚谈“市民权”,不仅于国家发展不利,而且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不像主流学者所宣称的那样“以农民为主体”。按照第一种方案,将土地增值收益都交给城郊农民,这对于非城郊农民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土地的增值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投资紧密相关,而与城郊农民的个体因素无关,因此城郊农民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没有理由独享这些增值收益。另外,中国的土地制度属于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因此土地的增值本质上是一项公有财产而不是私有财产。由城郊农民独享土地增值收益,最终只会培育出一个食利阶层,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分化。按照第二种方案,非城郊农民拿自己的土地置换“市民权”,其结果是强化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和生活风险。中国城市化之所以比较稳定,其奥秘在于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模式,老年人在农村种田完成家庭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年轻人则外出务工为个体家庭的城市化累积资源。这两笔收入结合起来,可以为农民提供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和一种可期待的城市化前景。一旦农民没准备好之前就丧失了农村土地,而只能一家老小蜗居在陌生的城市、冒着极大的失业风险战战兢兢地活着;老人在城里就不了业,也无法通过种田弥补家用;年轻人也只能到沿海城市继续打工养家糊口,他们的家庭依然是不完整的,而且生活压力更大。一旦经济不景气,大批农民工失业又无法回到农村种田,恐怕社会就不会那么稳定了;除非国家能够把所有农民都养起来,但是正如贺雪峰教授所讲的,如果国家为所有进城人口都提供体面的城市生活,则中国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地价所综合形成的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优势就不复存在,中国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种方案是相对合理的,即农民不需要拿自己的土地置换“市民权”就可以分享城郊土地的增值收益,但是这种观点非常不主流。而且因为反对政府分享部分的土地增值收益,城市化所需的基础设施成为一个难解的问题,最终也会影响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3回归“市民权”的本质
如此看来,虚谈“市民权”误国误民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但为何很多人看不清楚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迷信权利的神话,以为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人民没有权利造成的,因此只有通过不断地赋权才能够走出困境。这种权利的神话甚至成为一种不可辩驳的道德话语,笼罩整个学术界和政策界。于是,土地要确权,要逐渐私权化;农民要赋权,要给予“市民权”。他们总是问:给农民更多的权利难道有害吗?而不问:给农民更多的权利难道有利吗?到底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权利?实际上,关于权利还有两个基本常识:一是“反公地悲剧”,二是“权利有成本”。其次是迷信市场的神话,以为中国所有的问题只要放到市场里面就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因此,土地问题应该交给市场,土地增值收益也应该通过市场来实现配置。然而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解决不了多数的公共品供给问题。正如贺雪峰教授指出的,在土地问题的争论中,最离奇的要数增减挂钩政策,主流学者经常把从农村置换出来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价格视为土地市场运作的结果,殊不知土地本身的位置根本无法挪动置换,所谓的指标价格仅仅是国家政策使然(第196-212页)。而“市民权”更是一种公共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显得稀缺,它是综合国力的一种权利形态,而不是市场运作的结果。最后是对政府的不信任,以为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做坏事。如果说这几年中国混乱的学术界有某些共识的话,那就是在搞臭政府名声这件事情上面同心同德。实际上这些学者没有搞清楚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少数政府官员做坏事;二是多数政府官员做坏事;三是政府的存在就是坏事。在现实生活中,到底哪一个才是主要问题呢?恐怕很多学者不调研不思考就已经有结论了吧。那么,是不是不可以谈“市民权”了?并非如此。实际上,“市民权”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权利形态,“市民权”的实现程度往往与国家综合实力(当然也包括国家权力和国家权威)成正比。一旦试图超越国家发展水平甚至脱离国家语境来强调“市民权”,就是一种虚谈,不仅误国,而且误民。因此,我们应当回到常识中来,重新审视我们国家在土地制度安排上的适应性与合理性。它一方面给了国家发展足够的回旋空间,以一个较低的成本和较低的风险来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它较好地统筹了城郊农民和非城郊农民的利益配置(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后者可以通过城乡之间的代际分工最大程度地稀释市场的风险和生活的压力。基于不同的机遇和能力,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农民市民化的深度和广度都会逐渐扩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多做客观的研究,少做无谓的虚谈。我想这也许正是贺雪峰教授的新书《大国之基》所要提醒我们的。